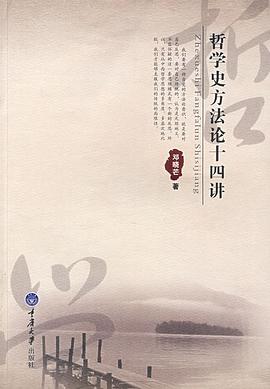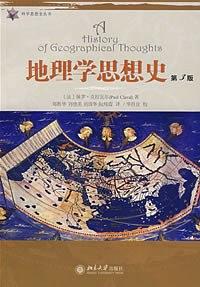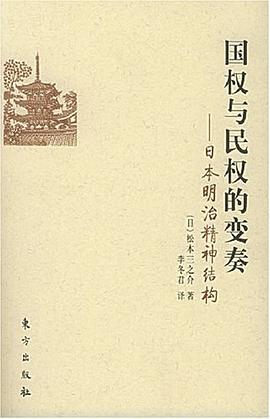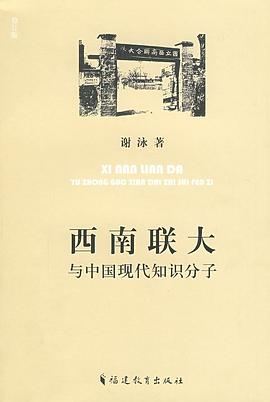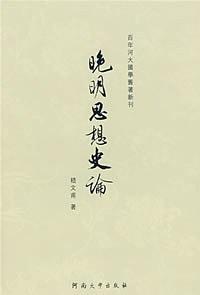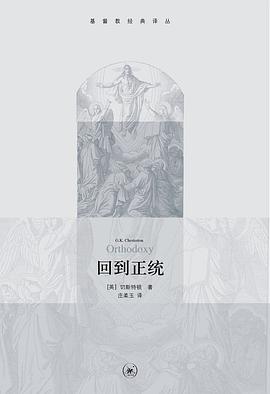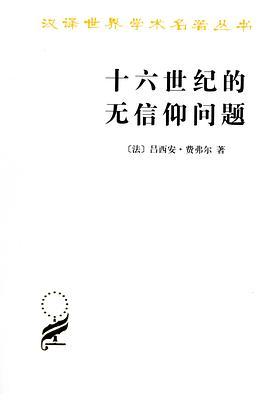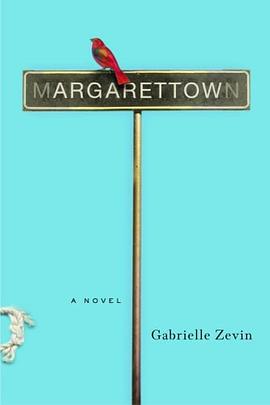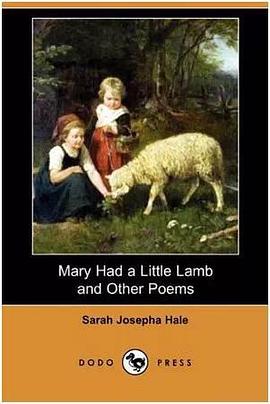具体描述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科学作为天职 马克斯·韦伯著 李康译
I 韦伯与他的时代 吉砚茹译
科学的天职 卡勒尔
科学的革命 特洛尔奇
韦伯论科学作为天职 库尔提乌斯
韦伯及其科学观 李凯尔特
哲学还是世界观学说? 舍勒
韦伯对哲学的排斥 舍勒
韦伯的科学观 洛维特
II 韦伯与我们的时代
“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韦伯与德国大学体制的论争 渠敬东
“科学作为天职”在中国
韦伯视角下的现代中国知识场域 应星
指向价值的行动
“科学作为天职”与韦伯科学学说中的价值理性化 田耕
专家没有精神?
韦伯论官僚时代的科学与文明 李猛
· · · · · · (收起)
读后感
(本体是本学期的一篇课程读书报告,略有改动) 提起马克斯·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或许多数非专业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其中一句“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1]],这句或许连本篇演讲的点睛之笔都不一定算得上的话,却长期作为入门者自励的“座右铭”,似乎大家都是狂热的...
评分 评分(本体是本学期的一篇课程读书报告,略有改动) 提起马克斯·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或许多数非专业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其中一句“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1]],这句或许连本篇演讲的点睛之笔都不一定算得上的话,却长期作为入门者自励的“座右铭”,似乎大家都是狂热的...
评分思想史上很少有谁的演讲能像韦伯阔论学术与政治的两篇演讲结成文字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反复阅读长盛不衰了吧?拿《科学作为天职》来说,这篇对科学在当代的命运透着悲观论调的演讲,何以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感,首先源自它是韦伯自己一生学术(及政治)事业的高度...
评分用户评价
天气渐寒,恰巧又见证了一桩“事件性事件”,多年以后再次重读韦伯的这个演讲(新译本),更觉萧索苍茫:“世界上各种不同(但同样有效)的价值秩序,彼此之间处于不可消解的争斗之中……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评分天气渐寒,恰巧又见证了一桩“事件性事件”,多年以后再次重读韦伯的这个演讲(新译本),更觉萧索苍茫:“世界上各种不同(但同样有效)的价值秩序,彼此之间处于不可消解的争斗之中……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评分现代学者需要面对体制化和专业化对人的桎梏。体制化是国家通过课题、项目、职称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干预、指导学术的发展,专业化是学术的规范和专业的边界形成对学者的“规训”。韦伯以及各位老师提供对抗的方式也许带有一些非理性的色彩,在课题项目发论文为王的时代,坚守一些不认同和不随大流,在人人都只敢在自己专业领域发声的时代,热情的推动跨学科的、打破学术壁垒的对话,踏踏实实的一点点做,相信心理上的成就和快乐会大于取得体制上成功的快乐。p.s田作为年轻学者面临很多实在的问题,很多话都不敢说,跟其他文章一比差距就出来了
评分在当今时代科学面临着专业化限制,科学发现的灵感和想法又受制于偶然和命运,科学本身又处于进步过程之中。由此引出科学的意义问题,韦伯想要让青年学者和学生明白:在这个世界祛魅的理性化时代,科学从业者首先必须承认价值、秩序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即诸神之争,在此更应该摒弃对人格和体验的偶像崇拜,科学还能使我们对目的/手段,实践/理论,政治/科学之间的有益分立产生清明的自觉意识。有志于科学的青年应该放弃单纯的拯救期待和渴望投身于工作当中。前面读的时候就想到韦伯与尼采、韦伯与新康德主义、韦伯与胡塞尔甚至与伯林。最后一篇李猛的文章真的傻眼了,从施特劳斯的魔眼看韦伯,从韦伯式崇高与伟大的失败谈,这个时候可能适合再返回去读一遍韦伯的演讲,包括以政治为业……可是时代的长夜可能已深了……
评分看了几位老师写的评论,科学其实蛮难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志者,应该首先好好活,再考虑怎么做好的问题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