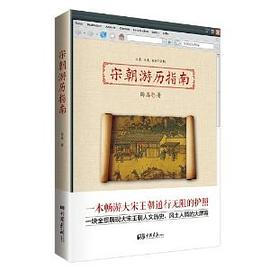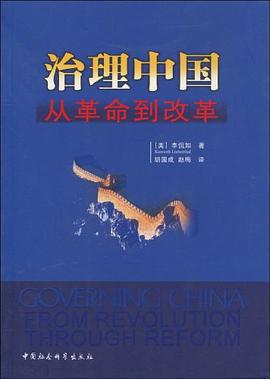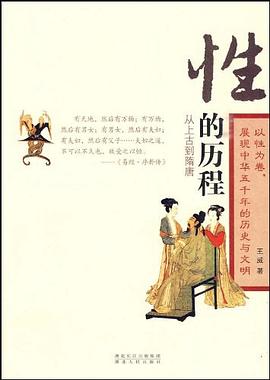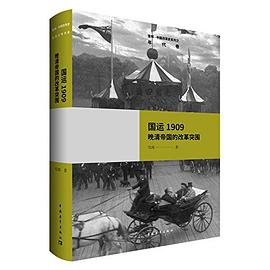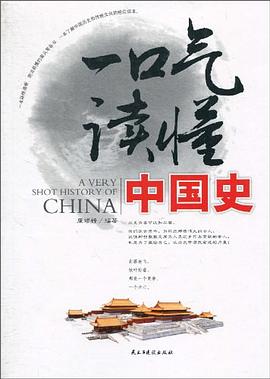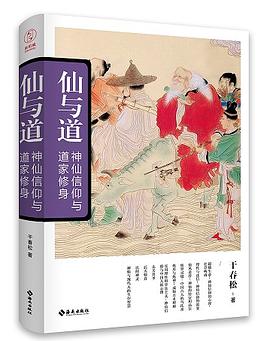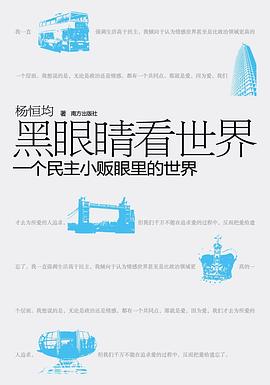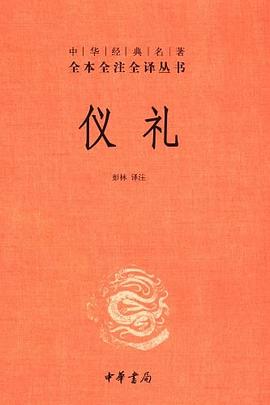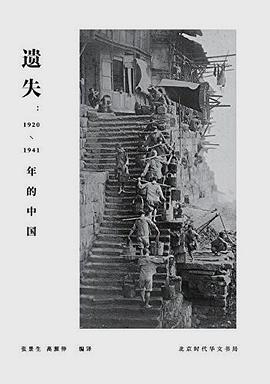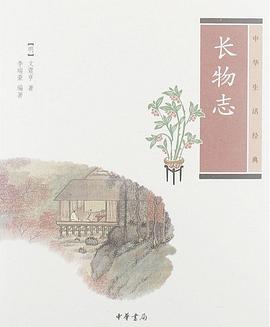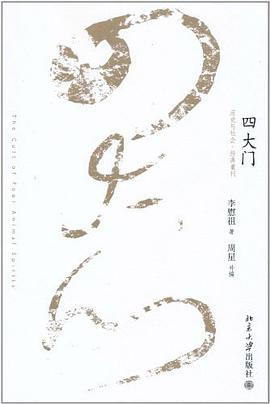具体描述
作者继续深入历史。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来,国家/流氓这一对偶制乃是历史循环其间的结构性巨型框架: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诗歌、小说)、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五四”迄今的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
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但当赵本山的小品被国家主义美学接受并赢得热烈而又广泛的群众呼声时,这表明流氓话语很可能具有软化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的确,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并不总是对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国家主义”,亦即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不是吗?我们正在倾听和叙说着诸如此类的话语。显然,当此话语变革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反讽、解构以及符号学分析,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他当真是耍惯了罗兰·巴特式的解剖美学经验的锐利手术刀——所谓的“朱体”由此生成,而《流氓的盛宴》是为集“朱体”之大成者。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它风姿绰约地充任了作者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经验的基本工具。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在此,它跟朱大可所批评的事物构成了极为有趣的互文关系。
作者简介
朱大可,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著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多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富有影响。
目录信息
一、流氓研究的不同论域
1、流氓的古代分类
2、狭义流氓学
3、广义流氓学
4、“流氓”和“流氓主义”的语义辨认
二、现有流氓学成果及其缺憾
1、流氓学简史
2、流氓学的主要类型
3、流氓研究的成就与缺憾
第一章 国家主义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一、 国家主义的话语转型
1、 国家美学的初次转型
2、国家美学的二度转型
3、红色话语的苏醒
4、帝国话语的泛滥
二、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
1、流氓国家主义的崛起
2、历史、对偶制和对偶循环
第二章 身份与话语:流氓的故乡
.中国社会的身份秩序
1、 三重身份的迷津
2、身份的辨认程序
3、身份秩序的间隙性瓦解
身份的修复
1、流氓之痛和身份焦虑
2、身份的修复
3、代偿与替身
第三章 流氓话语:反讽的新世界
一、 色语、酷语和秽语
1、色语:密室生涯的终结
2、酷语风行数千年的公共话语
3、秽语(脏词):父权对母权的政变
二、 流氓叙事
1、 言说与书写的叙事功能
2叙事中的流氓偶像
三、 阅读与书写的反讽
1、话语的正谕体系
2、话语的反讽体系
四、当代流氓主义的话语模式
1、当代流氓主义的日常美学
2、现代流氓话语的基本类型
第四章 1920~1960:当代流氓话语的历史起源
一、“五四”和“新文化”:酷语的起源
1、五四运动的身体酷语
2、新文化运动的酷语关键词
3、“新流氓主义”:酷语、色语和秽语的起源
二、酷语的演进:鲁语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1、“鲁语”的崛起
2、“恨语”及其鞭子语像
三、上山下乡:新流氓话语的摇篮
1、红色流氓的政治挫败
2、地下沙龙:意识形态的反叛象征
3、民间话语的三位一体
第五章 1980:新流氓话语的租借与复兴
一、 八十年代的流氓语境
1、新流氓起源:身份的总体危机
2、酷语的租借
3、色语的租借
4、流浪话语的租借
二、崔健摇滚:本土流氓话语的崛起
1、中国摇滚的诞生
2、崔健:一无所有的流氓..
第六章 非非、莽汉、撒娇:流氓话语的诗歌摇篮
一、 先锋诗人:流氓话语的先驱
1、流走的命题
2、校园先锋主义
3、第三代实验诗歌大展
二、“非非主义”和流氓美学
1、话语革命来了
2、第一个“下本身”
三、“莽汉主义”与草莽诗学
1、口语大爆炸
2、盲流的游吟诗人
四、撒娇派及其犬儒哲学
1、耳朵的失误和诗歌夜莺的歌唱
2、新犬儒主义的兴起
第七章 王朔主义:众痞的玩世喜剧
一、 小说反讽的苏醒
1、刘索拉与学院嬉皮文学
2、徐星:流氓叙事的先驱
二、“王朔主义”的诞生
1、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话语的复仇
3、王朔式反讽
三、电影与美术的视觉变法
1、第五代导演的话语变法
2、视觉艺术的颠覆运动
第八章 1990~2000:文学里的流氓面容
一、 痞子短语和流氓的面容
1、文化衫和泼皮短语
2、新痞子主义造型的诞生
二、乡村叙事:农民的仇恨与暴力
1、杨争光的方言叙事
2、莫言的肉刑之歌余华的喋血书写
三、流氓小说三部曲:手淫物语
1、 废都,北方旧文人的阳具
2、米:江南流氓的欲望和病毒
3、王小波:色语大爆破的英雄
四、从优雅色语到自戕的尊严
1、虹影的优雅色语
2、棉棉:话语的自戕
第九章 口语、口吃、口交:后流氓主义的夜宴
一、 口语地带:“新父亲”的面容
1、新口语小说:美元下的身份辨认
2、反讽叙事和正谕批评的冲突
二、口吃时刻:“结结巴巴”的先锋诗歌
1、伊沙的文化口吃
2、民族图腾和小便叙事
三、口交世代:“下半身”的造反宣言
1、 “下半身”审判“上半身”
2、生殖器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盘峰论战”:茶壶里的风暴
口语还是书语,这是一个问题
2、群雄逐鹿话语权力场
五、 学术国家主义的崛起
1、国学复兴和“人文精神”讨论
2、知识界大裂变
第十章 视觉符号的解构运动
一、 行为艺术:吃婴还是弑父
1、行为艺术年:2001的暴力叙事
2、“吃婴”和行为艺术的孤立状态
二、纪录片的流氓主义视界
1、吴文光的“流氓关怀”
2、何处才是流浪的“彼岸”
3、记录美学:第一现场的目击证人建筑的非国家主义化
三、建筑的非国家主义化
1、摩天大楼的阳具政治
2、高楼顶部的“形而上学”
3、帝王话语的解体
第十一章 消费叙事、大话革命和符号资本
一、“消费叙事”及其流氓(妓女)的转型
1、蝴蝶的尖叫
2、乌鸦的舞蹈
二、白与黑:摇滚的裂变
1、九十年代的摇滚疗法
2、何勇:愤怒与退离
3、张楚的小男孩心语
4、地下摇滚的隐形滚动
5、摇滚以外的油滑声音
第十二章 大话、哄客和灵语失踪案
一、零年代的大话美学
1、脂粉英雄的无厘头话语
2、网络群众的大话运动
3、零年代的游戏综合症
二、话语权分化和哄客的诞生
1、话语权的重新洗牌
2、丑角美学的诞生
三、酷语和秽语的蒙面表演
1、酷语者的网络冒险
2、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四、色语的策略、逻辑及其敌人
1、色语的递进策略
2、2005,娱乐元年的女人们
3、色语的四种逻辑
五、“身语”和“灵语”的世纪交战
1、灵语失踪案
2、伪灵语和“第四代”儒生
六、结语: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
附录 流氓的精神分枷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被误读的流氓 ——评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流氓的盛宴》出版后, 朱大可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无欣慰且感慨的写道,“这部著述的出版,历经三年,走了将近60家出版社,最后才在作者对书稿充分自阉之后,由新星出版社接纳,获得出生证。”但是朱大可...
评分庙堂/江湖、国家/流氓、正谕/反讽的对偶性阐释框架是朱大可的巨大成功,也是朱大可当下的失败,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文本巴洛克式的华丽藻饰是朱大可的巨大的成功,也是朱大可当下的失败,他的形式已经套路化,无处不“散发”着日暮穷途的腐败“气息”。 可以自由实现修辞操作的...
评分被误读的流氓 ——评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流氓的盛宴》出版后, 朱大可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无欣慰且感慨的写道,“这部著述的出版,历经三年,走了将近60家出版社,最后才在作者对书稿充分自阉之后,由新星出版社接纳,获得出生证。”但是朱大可...
评分上个礼拜分别收到别人发来的“08年非主流最受欢迎的个性签名”和“非主流QQ头像下载”的网站。 第一个网站上是我写过的缎子的网页,编辑这个网页肯定别有用心或者有所偏好,摘抄的都是一些我写过比较有颜色的缎子,我纯情的一面完全没法得到展示。 我纯情么?多少有点吧,虽...
用户评价
我不得不提一下这本书的配角群像塑造,简直是神来之笔。很多时候,配角的光芒甚至盖过了主角,每一个小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人生弧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性格鲜明,对话火花四射,读起来丝毫不会感到脸谱化。我特别喜欢那个总是爱开玩笑却又在关键时刻一语道破天机的角色,他的存在为紧张的剧情增添了一抹难得的亮色。作者在处理群体关系和派系斗争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洞察力,那种微妙的权力制衡和暗流涌动,描绘得入木三分,让人不禁思考现实中的人际复杂性。这是一部真正群星闪耀的作品,缺了任何一颗星都会黯淡许多。
评分这本书的想象力真是天马行空,故事的构建宏大而精巧,每一个转折都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作者对世界观的设定简直令人叹为观止,那些光怪陆离的设定和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让人仿佛真的踏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维度。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细细琢磨那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隐晦的伏笔,那种抽丝剥茧的阅读体验,既烧脑又过瘾。尤其是主角的成长线,那种从迷茫到坚定的蜕变,刻画得极其细腻真实,让人感同身受,恨不得自己也能一起并肩作战。整体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部构建完整的史诗,值得反复品味和研究。那种沉浸感,是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作品能够给予的,完全把我的业余时间填满了,连睡觉都在想后续的情节发展。
评分说实话,我一开始对这种题材并不抱太大期望,总觉得会是老套的英雄主义叙事,但翻开这本书后,立刻被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抓住了。文字的质感非常独特,时而冷峻如冰,时而热烈如火,特别是对环境和气氛的描写,简直可以用“身临其境”来形容。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用最朴实的词汇,勾勒出最华丽的场景。我特别欣赏它对人性复杂面的挖掘,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灰色地带和无法言说的苦衷,这种深度让整个故事的层次感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读完最后一页,我甚至有些恍惚,感觉自己才从那个世界里抽离出来,那种情绪的余韵久久不散,让人回味无穷,甚至有些怅然若失。
评分这部作品的节奏把控堪称教科书级别。开篇的铺陈张弛有度,不急不躁地抛出悬念,引人入胜,而一旦进入主线,情节的推进速度便如同脱缰的野马,高潮迭起,让人肾上腺素飙升。我很少遇到能将动作场面描写得如此清晰流畅,又不失文学性的作品。拳拳到肉的搏斗,精妙绝伦的智斗,都被作者用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呈现出来。我甚至能想象出电影分镜的样子。更难得的是,即便在高强度的情节冲突中,作者依然没有忘记植入一些关于哲思和命运的探讨,使得这部作品在刺激之余,又不失思想的厚度。非常适合一口气读完,体验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评分从装帧设计到内页排版,这本书的实体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纸张的触感温润细腻,字体大小和行距都非常舒适,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内容上,作者对一些专业领域的知识似乎做了非常详尽的考据,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其中穿插的那些技术细节或者历史背景的引用,都显得非常扎实可信,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说服力。它不仅仅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的途径,更像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和思考的平台。对于追求阅读体验和内容深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近几年内值得珍藏的佳作,我已经把它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了。
评分大学时读的。语言密度高,尤其是各种四大。
评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枚流氓
评分超级好看啊!!!!
评分邪门
评分有一个华丽的学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