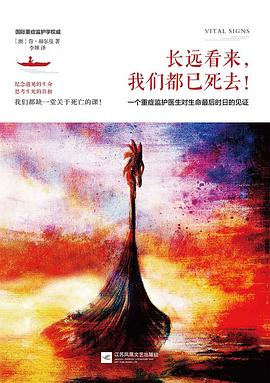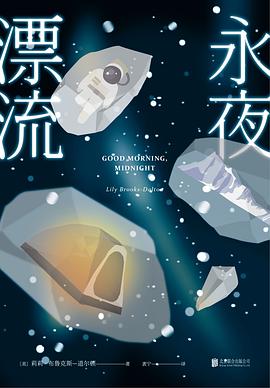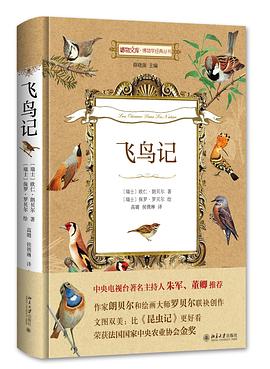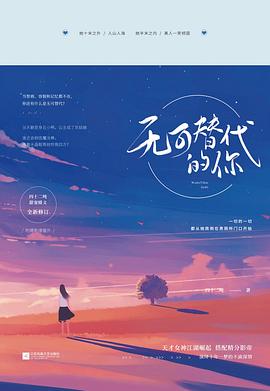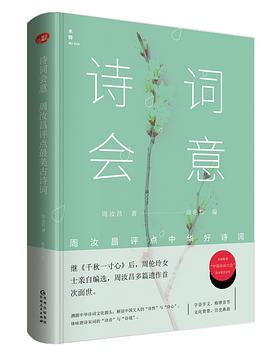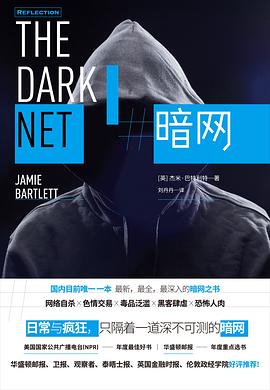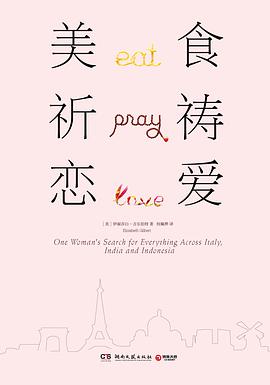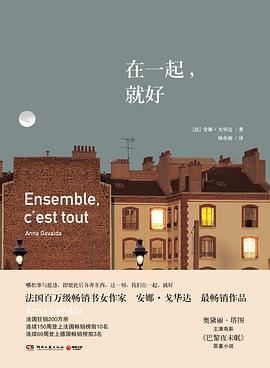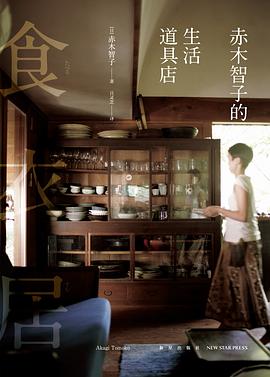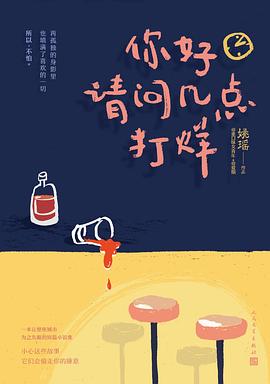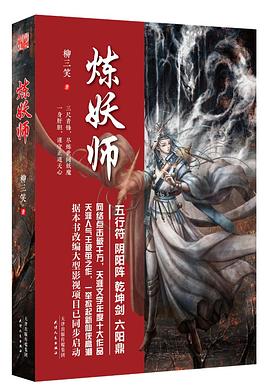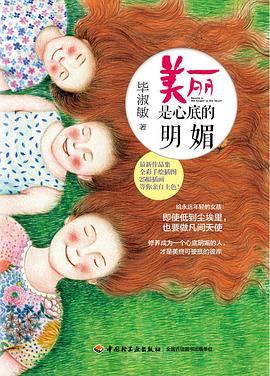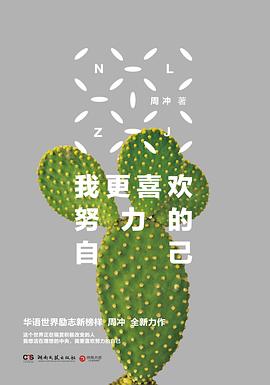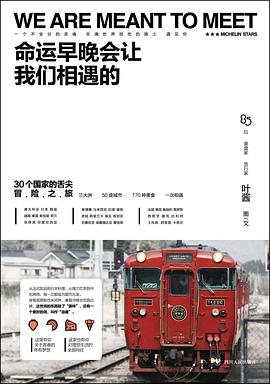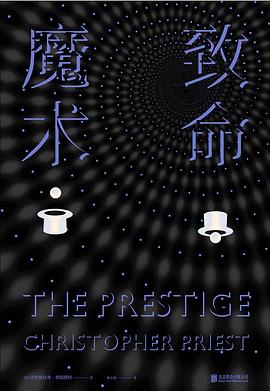具體描述
本書是奧地利學者、古典語文學傢雷立柏的破執之作。雷立柏紮根北京二十餘載,在這本書中,他以“世界公民”與“文化橋梁”的視角,將自己對北京深沉的感情傾注於文字,並憑藉其學貫中西的學識,旁徵博引,縱論古今,或從語言、文字、曆史、藝術、宗教等諸多細微之處挖掘那些鮮為人知的、被淹沒的曆史,或以全新視角解讀那些為人熟知的曆史,在文化的相遇與碰撞中破除迷執。
著者簡介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語文學傢。1967年生於奧地利,1985年進入大學學習哲學、宗教學及基督教神學。1988年至1991年在颱北輔仁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哲學。1995年在奧地利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到北京,考 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班,師從湯一介先生和陳來先生,於1999年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進行翻譯和研究,並開始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2004年2月至今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開設“拉丁語基礎”“古希臘語基礎”“拉丁語文學史”“古希臘語文學史”“歐洲中世紀文學史”“古希伯來語”等課程。
圖書目錄
vi | 一個世界公民——孫 鬱
xi | 自序:外國人應該愛北京的101個理由
001 | 首 都
003 | 祖先之地
005 | 國際化的開始
012 | 北京——我的母親
015 | 我的名字是“雷”
018 | 雷師的排位
024 | 從和林到北京
026 | 北京的地名
030 | 順天府
039 | 法律和正義
044 | 北京精神
049 | 徐光啓和利瑪竇,李自標和馬戛爾尼
053 | 公共利益和拉丁語ius
058 | 北京和香港
062 | 北京和汽車的關係
069 | 北京定星期天為休假日
072 | 大毛子和二毛子
079 | 羅馬的水泥和北京的樓房
082 | 都靈和靈都
085 | 漢語的感嘆詞和拉丁語的感嘆詞
087 | 中國人關於意大利的最早報告
092 | 第一位留學生“鄭先生”
098 | 白晉和漢字的深奧意義
101 | 北京的美女和纔女
104 | 香 山
106 | 雷叔叔之一:雷孝思
110 | 雷叔叔之二:雷登
114 | 雷叔叔之三:雷永明
119 | 北京的動物
125 | 北京的西堂
129 | 北京的名稱
133 | 北京第一批留歐的學生
136 | 我最佩服的北京女士
141 | 我最佩服的北京人英斂之
144 | 知識傳播和謠言
152 | 英斂之辦學
160 | 我和愛新覺羅的關係
164 | 在北京齣生的孩子
172 | 北京和白話運動
184 | 外國人給中國帶來什麼?
190 | 北京的“魔鬼”:無知
193 | 北京的牙醫
196 | 被遺忘的漢學傢鮑潤生
200 | 北京,我的肺腑,我的血肉!
203 | 中國畫和西方畫
212 | 北京唯一的一所大學?
223 | 貫穿北京曆史的機構
229 | 中國最古老的西文圖書館
235 | 北京的外國人迴來瞭
239 | 我的精神傢園
243 | “我的”北京曆史大事錶
· · · · · · (收起)
讀後感
本文载于2017年6月24日 《新京报·书评周刊》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编辑:张畅,张进。 原文出处 雷立柏:精神使人活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Matteo Ricci(利玛窦)来到北京,进呈自鸣钟、万国舆图等物,以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布道,同时把中国的科学文化推介到欧洲。 四百...
評分 評分 評分用戶評價
A self-assuring racist with a missionary agenda whose academic credibility is highly dubious.另,新星齣版社的編輯是被傳教洗腦瞭吧,忍著惡心看瞭三分之一掀桌瞭
评分大白話講自己對北京的真情實感,坦誠的令人感動。當然,基督徒的視角也太過於明顯,不過倒也符閤“靈”都的標題。雷是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為目標的新時代“傳教士”,倒也可以理解他的寫法。無論如何,他對於中西文化傳播交流做的冷闆凳苦功夫如何贊美都不為過。
评分忘瞭具體寫的什麼瞭,隻記得我想把書給撕瞭
评分大白話講自己對北京的真情實感,坦誠的令人感動。當然,基督徒的視角也太過於明顯,不過倒也符閤“靈”都的標題。雷是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為目標的新時代“傳教士”,倒也可以理解他的寫法。無論如何,他對於中西文化傳播交流做的冷闆凳苦功夫如何贊美都不為過。
评分語義學主宰著雷老師的思維,純粹的學人的生活並沒有那麼有趣,加很多感嘆號的情感錶達也總難讓人信服。盡管同何偉這樣的作者相比並不很恰當,但久居中國,卻對中國人沒有什麼感想,隻在種種詞源裏找過去,也的確難以引人共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