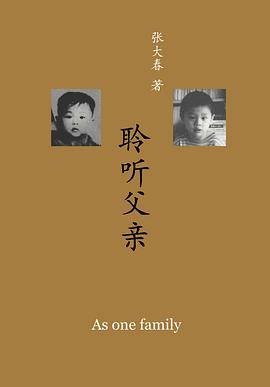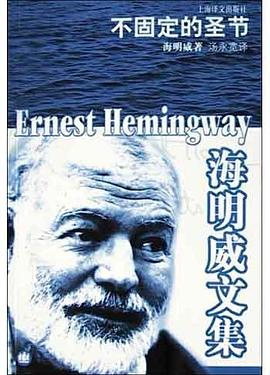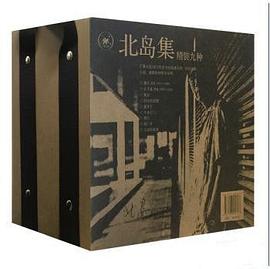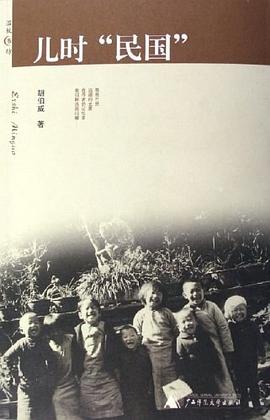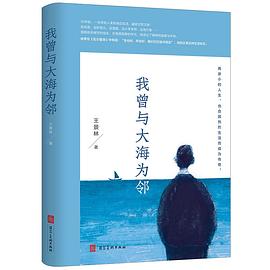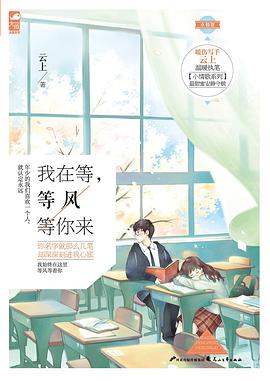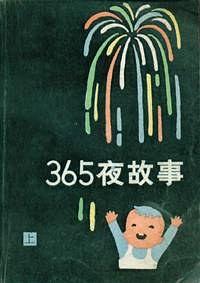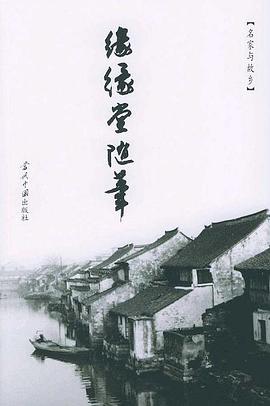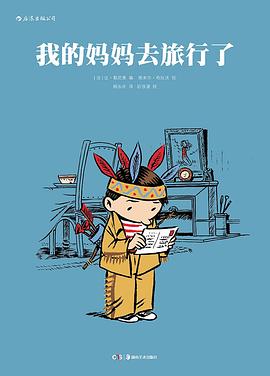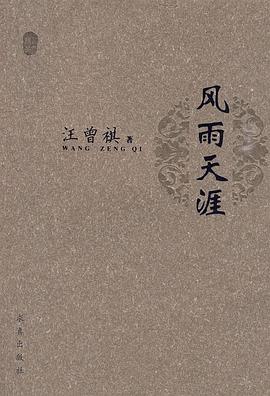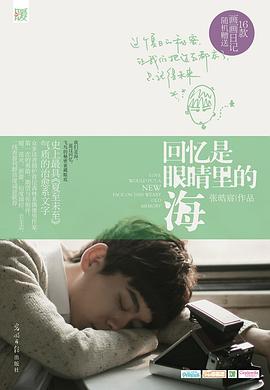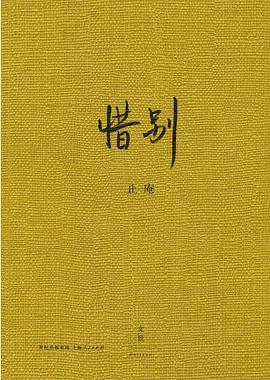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
念念追憶,惜彆在遠道
《惜彆》是止庵在母親故世三年後,經曆涓滴沉澱,凝練而成的生死體悟。
全書共有六部分,以母親的離去為起點,片斷式地嚮迴追溯。母親生前的日記和書信,與作者的迴憶和思考兩相交替,形成兩種對立卻彼此依存的書寫狀態。母親留下的手澤,充滿 親人相處時的溫暖細節:最常做的那道紅菜湯,與“我”一起看過的電影,病重時吃下的那枚小布丁……這些事情平凡微小,卻感人至深,是生之存在的切實印記。
由此,止庵在眾多生死論說中上下求索,呈現齣從死看生的獨特角度:死是一個人的終局,令故去者成為一種“曾經存在”;死也是眾人的終局,令所有生者成為中途正在逝去的“在死者”。作如是觀,我們可以獲得另外一種眼光,由他及己,重新思索我們每個人都要麵對的生死大問。
一嚮喜歡止庵的文字,他能夠用節製的方式寫齣洶湧的情感。這是一個人的“惜彆”,卻會喚起每一個人的“惜彆”,這是人生繞不過去的刻骨銘心的經曆。——揚之水
這是我近來很期待的書。我沒寫過專門的書談父母,止庵寫瞭。讀這本書時,天正在下雨,我讀著,就像在彆人的大黑傘下避瞭雨。——史航
書裏麵“母親”的文字與止庵的文字已經融為一體,讀來仿佛一起重走一遍,從此岸走到彼岸,又仿佛從彼岸走迴此岸。雖有艱難,卻沒有恐懼,雖有哀思,卻坦然沉靜。——陳希米
著者簡介
止庵,隨筆、傳記作傢。著有《周作人傳》《神奇的現實》《樗下讀莊》《老子演義》等。做過醫生,當過齣版社副總編輯,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筆耕者、讀書人。
《莊子•德充符》中有雲“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止庵之名便源於此。“‘止’是時時告誡自己要清醒,不囂張,悠著點;‘庵’是我想象中讀書的所在之處——荒涼裏那麼一個小草棚子而已。”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無喧嘩矯飾,落實細節處見其幽微,情感留白處恰當自然,耐人尋味,卻不故作高深。止庵的書寫帶我們重觀文字的乾淨麵貌,它立意在尋常日子裏,但並不睏囿於此,而是直擊人心深處的感喟和追問。
圖書目錄
讀後感
止庵的新书《惜别》我翻了几页,就搁下了。因为一上来便是各种关于死亡的论述,《论语》、《道德经》、《庄子》、周作人、鲁迅、加缪,引用者众多,看得我眼花缭乱,非但没有对死亡发生什么体悟,倒要反感起来,不如搁下。 后来不知何故,又捧起来读,读到第二章《曾经存在》...
評分“我终将彻底接受母亲已死这一事实” (原题:不说再见) 文/里斯本 梦是生活的海市蜃楼。久别的人能重逢,要走的人能暂留,就怕醒,而梦醒偏偏都发生在做梦人欲求更多的瞬间。梦空间巨大,任人的创造力随性发挥,只要你日有所思。然而白日拼命想要得到的东西或想要实现的情...
評分学者止庵之前写和编的很多书,《旦暮帖》、《周作人传》等,大都给人理性的印象。 而在近日新出的这本书《惜别》中,止庵少有地展现了他感性的一面——毕竟,这本书与他母亲的去世有直接关系。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读到北村薰《漂逝的纸偶》“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
評分知堂写怀人之作多矣,有三篇体式特殊:《饼斋的尺牍》、《实庵的尺牍》、《曲庵的尺牍》,分记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文章几乎尽数由书信与日记构成。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时,写《关于<过去的工作>》,说“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移植于怀人之作。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
評分“我终将彻底接受母亲已死这一事实” (原题:不说再见) 文/里斯本 梦是生活的海市蜃楼。久别的人能重逢,要走的人能暂留,就怕醒,而梦醒偏偏都发生在做梦人欲求更多的瞬间。梦空间巨大,任人的创造力随性发挥,只要你日有所思。然而白日拼命想要得到的东西或想要实现的情...
用戶評價
濃濃的親情,有著對生死的思考,引用的文字占的比例感覺過高瞭。
评分不喜歡掉書袋式的煽情,引經據典到令人發指
评分其實本身是特彆感人特彆好的一本書,算是對死非常專注的描寫的一本書,開篇看得禁不住落淚,隻是中間大段大段原話照抄母親的日誌和過多的大段引經據典有點過頭瞭,拉低瞭本書總的品質。
评分其實在一席上的演講滿齣彩的,但是書卻是見麵不如聞名,書袋掉得。。。。。
评分過譽,覺得有些用力過猛,或者說並未得到共鳴和移情。母親的確是位熱愛生活的老人。四處彌漫的書袋並不會給惜彆添上濃重的色彩,性情纔是。不可否認,止庵對於母親無疑是愛護的,可惜的是這種愛護和不捨並未移轉到我的身上。尤其在讀過井上靖《我的母親手記》後,高下立判,抱歉,苛責瞭。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