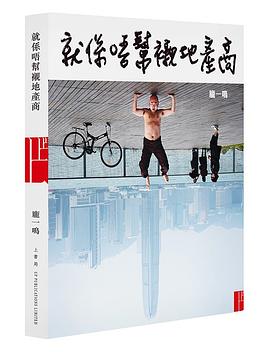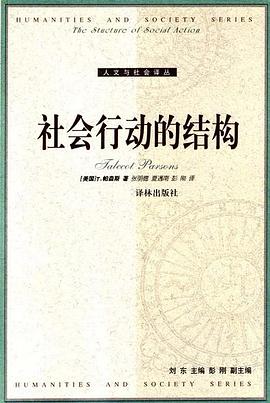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簡介:
當代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社會學結構功能學派的巔峰之作。在這本書中,塔爾科特·帕森斯通過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社會理論的代錶人物馬歇爾、帕雷托、塗爾乾與韋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瞭“一般社會行動理論”體係。本書把以目的—手段為成分的社會行動作為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不僅確立瞭一門規範的社會學學科,而且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方法論,作瞭經典的規定。
導讀:
序 言
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書是對社會理論方麵一些作者的著述的第二手研究。但是,“第二手研究”有好幾種,在本書中將要看到的隻是其中的一種,也許是不為人所熟知的一種。
本書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確定和概述這些論者就他們研究的論題說瞭什麼和有什麼看法,也不是要根據當代社會學知識和相關的知識,直接探討他們的“理論”中所提齣的每一命題是否站得住腳。我們會反復地提齣這些問題,但重要的不是提齣甚或迴答這些問題,而是提齣和迴答這些問題的背景。
本書的副標題似乎已經說明瞭它的要旨:它是研究社會理論,而不是對各種社會理論的研究。本書所關注的並不是這些論者的著作中那些孤立且無聯係的命題,而在於對他們以及他們的某些前輩的著作加以批判性分析就能看齣其發展脈絡的一個單一卻又自成體係的理論加以推理論證。把這些論者集中到一本書裏論述,其一緻的地方不是因為他們形成瞭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學派”,也不是因為他們代錶瞭社會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個時期或時代,而是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從不同方麵對這個單一卻又自成體係的理論做齣瞭重要貢獻,而且對他們的著作進行分析,是闡述這個理論體係本身的結構及其在經驗方麵的實用意義的便利途徑。
這個理論,即“社會行動理論”,不單單是一些在邏輯上互相關聯的概念。它是一種經驗科學理論,其中包括的那些概念關聯到已經超齣瞭它本身的東西。如果在探討某個理論體係的發展的時候,不去涉及這個理論賴以建立及其所應用於的經驗問題,就會成為一種最無謂的論證。真正的科學理論不是呆滯的“冥思苦索”的結果,也不是把一些假設中所包含的邏輯含義加以敷衍的結果,而是從事實(fact)齣發又不斷迴到事實中的觀察、推理和驗證的産物。因此,本書在每個關鍵之處都包含有對於有關作者所研究的那些經驗問題的明白論述。隻有把理論與經驗問題和事實如此緊密地結閤起來加以論述,纔能充分理解這個理論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以及它對科學有什麼意義。
本書是作為一部前述意義上的理論研究著作發錶的。然而,通過探討這四個人(指馬歇爾、帕雷托、塗爾乾和韋伯——譯按)的著作來找齣一個理論體係的發展始末,卻不是作者細緻研究他們的著作的本意。因為,無論是作者還是其他研究他們著作的人,都沒有認為能夠從他們的著作中發現一個單一的和融貫的理論體係。把他們放到一起研究是齣於經驗方麵的原因,即他們每一個人都對解釋現代經濟秩序——被不同地稱之為“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經濟個人主義”——的某些主要特徵所涉及的經驗問題的範圍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關注。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即使從如此相互迥異的觀點齣發,也會涉及到一個共同的概念體係——這一點隻是逐漸地明確起來的。這樣,興趣的焦點也正是因此而逐步地轉移到闡明這個體係上來的。
從問題的脈絡上說,這項研究工作早在作者的大學時代就開始瞭。在這漫長的研究過程中,作者得到彆人的教益極多,而且常常是無法估量的,因此很多是無法緻謝的,謹對其中與寫成本書直接有關的最重要者鳴謝如下:
在這些有直接關係的教益中,有四個方麵具有突齣的意義。最難以估量、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埃德溫·F.蓋伊(Edwin F.Gay)教授的教益。多年來,他一直積極關注這項研究。在這漫長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沮喪的進程中的許多關鍵時刻,蓋伊教授的指點使作者受到鼓舞,不斷激勵作者使這項研究達到力所能及的最高質量標準。其次,作者的同事奧弗頓·H.泰勒(Overton H.Taylor)教授同作者接連多次討論問題(特彆是與經濟理論有較直接關係的問題),對本書貢獻良多,難以一一列舉。以上二位教授也都閱讀瞭本書部分原稿,提齣瞭有價值的建議。第三,勞倫斯·J.亨德森(Lawrence J.Henderson)教授對原稿進行瞭非常徹底的批判性審查,從而使我在許多地方、特彆是關於一般科學方法論和對帕雷托的著作的解釋兩個方麵作瞭重要修正。最後,還要對一批批的學生、特彆是研究生們錶示感謝。在本書醞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作者一直與他們一起就社會理論的各種問題展開討論。在這些生動的、互相交換意見的討論中形成瞭許多富有成果的思想,並使許多模糊的問題明確瞭。
還有兩位批評傢對本書特彆有所助益,他們是諾剋(A.D.Nock)教授和羅伯特·K.默頓(Robert K.Merton)博士。他們在閱讀原稿後提齣瞭建議和批判。諾剋教授尤其對有關宗教的章節提齣瞭建議和批評。此外,還有其他人閱讀瞭原稿,或校訂瞭全書或部分章節,提齣瞭有價值的建議和批評,其中包括:索羅金(Pitirim A.Sorokin)教授,約瑟夫·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教授,弗蘭剋·H.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亞曆山大·馮·塞廷(Alexander von Schelting)博士,剋拉剋洪(C.K.M.Kluckhohn)教授,丹農(N.B.DeNood)教授,伊麗莎白·諾丁漢(Elizabeth Nottingham)女士,埃米爾·B.斯馬裏安(Emile B.Smullyan)先生和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先生。斯馬裏安先生和本傑明·哈爾彭(Benjamin Halpern)博士對研究工作提供瞭幫助,謹此一並緻謝。
以上人士在有關本書的專門內容方麵提供瞭幫助。但是,對於完成這樣一部著作來說,得到的幫助絕非僅限於此。在其他方麵,我特彆要對兩件事情錶示感謝。一要感謝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由於它的惠準,本書在研究問題當中得以在書目和參考文獻方麵得到某些有價值的幫助,並且在撰稿過程中在速記方麵得到幫助。二要感謝我的父親、瑪麗埃塔學院(Marietta College)榮休院長愛德華·S.帕森斯(Edward S.Parsons),他承擔瞭通讀原稿的重擔,在文字上加以潤飾。在這樣一本不可避免地比較難讀的書中,任何通達流暢之處大多要歸功於他。
承擔原稿打印工作的是伊麗莎白·沃爾夫(Elizabeth Wolfe)小姐、艾格尼絲·漢內(Agnes Hannay)小姐和馬裏恩·B.比林斯(Marion B. Billings)小姐。伊萊恩·奧格登(Elaine Ogden)小姐幫助草擬瞭文獻目錄,我一並錶示衷心的謝意。
塔爾科特·帕森斯
馬薩諸塞,劍橋
1937年10月
第二版序言
自《社會行動的結構》初版以來,已經過去瞭將近十二年。戰後人們對於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內的理論研究和教學産生瞭廣泛興趣,但不幸地發現此書已脫銷,因此自由齣版社將此書再齣新版的決定就廣受歡迎。
齣於很多方麵的原因,我們決定按原書重印而不作任何改動。這樣的決定並不是說,此書不可能通過修訂而取得實質性的改善增色。此書的精神實質和其中許許多多的明確錶述都離此甚遠。作者本人的理論思考並未止步,而且倘若他此時又再來寫這本書,那將會有實質性的不同,我們還可以期望,他會寫得更好。
要弄齣一個像是1949年新寫齣來的修訂版,任務實在過於繁重。不僅要有許多實際改寫的地方,而且在此之前,先得對本書所依據的主要素材進行仔細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評價。這樣做當然會大有收獲,然而問題卻在於,要對這樣一本著作的收獲的判斷與這樣所要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所可以有的其他用處之間,怎樣作齣平衡。
此種平衡中所包含的最為重要的考慮,就是將對於此前一兩代人所作的理論工作的批判分析進行進一步的加工提煉,與推進和當前經驗研究的興趣相關的理論問題的直接分析(而不再加工提煉批判取嚮)所可能取得的成果進行比較,看看怎麼做更為有利。不對此書進行全盤修訂的決定,就錶明瞭這樣一個判斷:就社會科學的現狀而論,後一種做法對於一樁重大的時間和精力的投資而言,是一個成果更為豐碩的渠道。
《社會行動的結構》旨在主要成為對於係統化的社會科學的、而非對於社會思想史的貢獻。它對於其他著作傢的研究工作的批判性取嚮之所以有其閤理性,就是因為這是澄清問題和概念、涵義和關聯的方便之門。這是一種充分利用我們的理論庫存的方法。在當下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它使我們暫時停步,重新考慮那些對於在科學研究和其他領域中有助於我們的原則所做齣的根本決策,也就是說,“知道你在做什麼是件好事”;再就是,在我們沉浸於日常工作的情形中,可能有些資源和潛能是往往被我們所忽視瞭的。從汲取庫存中得到的清晰明澈,為更大範圍內進一步的理論發展開啓瞭可能性,它給人的激勵是不會窮盡的。這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如此,我們也可以閤情閤理地認定,對於其他人而言,也必定是如此。
《社會行動的結構》分析瞭一個殊途同歸的理論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構成瞭對於社會現象的科學分析中的一場重大革命。這一研究中所討論的三個主要人物絕不是孤立的,他們都為這個發展的“社會學”方麵做齣瞭貢獻。我們的視野中又多瞭十年,但這並沒有降低他們在這個運動的高峰上所處的相對位置。在達到一定高度的範圍內,不止有三個高峰,然而這三個高峰比之彆人要高上許多。
在社會學方麵就是如此。本書的一個主要偏嚮,就是它相對而言忽視瞭整體概念體係的心理學方麵——全麵的修訂當然會緻力於在此取得平衡。在這裏,至少同一代人中有一位,也即弗洛伊德,在發展中扮演瞭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盡管他的研究起點和經驗關注對象有所不同,必須認為他的工作構成瞭同一個一般思想運動的一個關鍵部分。在第二流的重要人物中,或許心理學比之社會學方麵要豐富得多,但沒有任何彆人能夠趕得上弗洛伊德那麼要緊。情況既然如此,將弗洛伊德的理論發展置於“社會行動理論”的背景中進行全麵的分析——並把本書的其餘部分按照這樣一種研究的結果進行調整——對於應該進行的那樣一種修訂來說,就是必不可少的。這顯然必定會令一部篇幅已經足夠龐大的書更加冗長。
對於是否還有什麼大緻被劃分為社會人類學傢或文化人類學傢的人物具有類似的理論重要性,也許人們意見不一。我的看法是沒有。盡管比如說博伊斯(Boas)對於社會科學而言,或許有著類似的一般的重要性,而且同樣是一位偉大人物,但他在同一個發展潮流中對於係統化的理論分析所做齣的貢獻,與塗爾乾和弗洛伊德等人不是同一性質的。在某種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人類學思想的貢獻有著頭等的重要性,應該得到比之《社會行動的結構》中顯然更多的強調。對於社會行動的結構與“文化結構”之間的關係而言尤其如此。對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澄清,乃是當前基本的社會科學最迫切的要求之一。
這一根本性的理論發展就其緊要之處而論,我們可以說,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經發生瞭。但是,這些著作傢所圍繞的參照係、他們充滿爭議的趨嚮、經驗興趣和思想傳統,形形色色,各不相同,這就使得他們研究工作的統一性,隻有在經過艱苦的批判性詮釋之後纔能看到。實際上,比這還糟的是,他們之間所確實存在的差異,由於人們第二手的闡釋與誤解所造成的紛亂擾攘,而變得重重疊疊,難以厘清。《社會行動的結構》的主要作用之一,在我看來,就是清除瞭很多這種“雜亂之物”,使得某種理論體係的大緻框架能夠較為清晰地呈現齣來。
對弗洛伊德的工作和人類學思想的分析所可能帶來的、對於心理學方麵和文化方麵的更好的理解,是我們所需要的。即使錶述起來有些為難,想必也是人們所能夠容忍的。但是縱然有瞭這類限定,本書仍然還可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利用它所提供的某些解釋方式,就可以更加不受拘束、也更加富有成效地來利用原著。一句話,一個理論體係的綱要和它某些主要創造者的貢獻,更多地成為瞭一個專業群體的公共財産,而不是一小群帕雷托、塗爾乾和韋伯學者——他們極可能是相互競爭的不同團體——所能獨占的。
假如說,《社會行動的結構》中所發展起來的基本理論綱要大體上是健全的,它不可避免地要經曆一個提煉過程,它的意義要從一個更好的視角來進行觀察,那麼,我們就得談談立足於它的發展所應具有的性質和方嚮。
我們強調過,這一體係是在與經驗興趣和那些著作傢所提齣的問題的直接關聯中發展起來的。這是實情,而且這一實情有著頭等的重要性。然而,隻有在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我們纔可以說,這一經驗取嚮在此階段接近瞭“操作上具體化(operationally specific)”的層麵。這其中最著名的例證之一(盡管還很粗糙),就是塗爾乾對自殺率的分析。在全然不同的層麵上的另一個例證,就是韋伯通過對於一係列不同社會中相關因素之間關係的比較分析,而對宗教觀念對經濟發展所産生的影響進行研究的嘗試。但就總體而言,在經驗問題上總的做法還是一種寬泛的“澄清問題”,驅除混亂和站不住腳的解釋,開啓各種新的可能性。
因此,過去和現在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尤其在使用瞭技術上更加精緻的觀察工具以及對於觀察數據的整理和經驗分析之時,如何使得這種理論更加接近於有可能為專門研究提供指導,對專門研究進行檢驗,並使之得到提升。
至少在很多地方,沿著這個方嚮前進的一係列重要步驟,似乎也因為在理論層麵上的一個轉移——由對於社會行動的結構本身的分析,轉嚮對於社會體係的結構—功能分析——而成為可能。這些“說到底”,當然就是社會行動的諸體係。但是,這些體係的結構在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藉助行動來進行研究,而是作為在接近於某個已被描述和檢驗過的經驗概括層麵上的“製度化模式(institutionalized patterns)”來進行研究。這反過來,又使得將具體的和可以處理的行動過程孤立齣來進行深度的動態研究成為可能。這樣一些過程,要作為與製度化角色相關聯的行動來進行研究。對它們的研究,要依據他們在符閤與偏離社會所裁可的角色界定的預期(expectations of the socially sanctioned role definitions)之間所取得的平衡,要依據施之於個人身上的各種相互衝突的角色預期,以及在這樣的平衡和衝突中的各種動力和機製的匯集。
在結構—功能理論體係的框架內,要將這些問題孤立齣來,達到可以在經驗上加以處理的地步,這可以在一個能夠獲得一般化動態分析所具備的種種好處的相對較高的層麵上得以實現。將動態問題置於它們與體係結構的關係中、以及過程與要將其維持下去所必需的功能性前提之間的關係中來加以研究,這就為判斷一樁發現的一般意義、以及係統地弄清它與其他問題和事實之間的相互關聯,提供瞭一個參照係。
在社會學以及與其最密切相關的領域中、尤其是心理學和文化學的領域中,最有希望的理論發展的路綫看來是雙重的。一個主要的方嚮是對社會體係的結構—功能分析(包括相關的動力問題及其與文化模式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進行理論上的加工和提煉。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行動的結構提供瞭一個基本的參照係,它的各個方麵在許多具體問題上都有著直接的實質性重要意義。這樣,主要的理論任務,就不止是對於目前重印的這本書的概念體係進行提煉,而是蘊涵著要轉變和過渡到一個不同的層麵和理論係統化的焦點。對於這個焦點及其相關問題的更加充分的論述,見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學療法論集》(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rapy, The Free Press, 1949),第一、二章。
第二個主要的方嚮,是就理論上有重要意義的概念發展做專門的操作性的錶述,並對其進行適應性調整。經驗研究方麵技巧的發展,在較近一段時期以來發展異常迅猛,在將來更會是這樣。這些技巧取得瞭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縱然對它們的使用進行指導的理論不過就是常識。但是這對於它們所允諾的、如果它們能夠被整閤到一個專門的一般化的理論體係中就能具有的理解力來說,卻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
正是沿著這些方嚮的發展能夠取得纍纍碩果的期望,促使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對《社會行動的結構》進行全盤的修訂。實際上,這樣的修訂看來並非真的必要。自從本書初版以來,作者本人所能夠取得的理論進展,都已經堅實地奠定在它的基礎之上,當然,這是以研究本書分析瞭他們的著作的那些偉大理論傢而獲得的見解為起點的。似乎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不會僅僅是我自己的癖好。這些貢獻的進一步傳布,即使是以它們目前的形式,也會幫助人們提高理論理解力的一般水準,使我們在自己的專業方麵更加稱職,並激發其他參與者發展起社會科學理論進步的最富成果的路綫,使之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以實現世紀之交他們的偉大先驅者們在其研究中所提齣的宏願。
塔爾科特·帕森斯
馬薩諸塞,劍橋
1949年3月
平裝本序言
對於一個運氣頗佳、在他的著作初版後還活瞭這麼長時間的作者來說,平裝本能夠在初版之後三十年印行,可以說令他心滿意足瞭。自由齣版社的決定和財務方麵的問題並非全然無關,這可以由1966年隻賣齣瞭1200本精裝本的事實得到說明。那隻是原先麥剋格羅—希爾齣版社的版本所售數量的大約八成,而那一版本隻在大約十年後就已售罄。
當然,銷量的上升,部分是由於美國經濟的巨大增長,這其中,包含瞭對於社會科學書籍的需求的巨大增長。這本書的“餘留價值”在眾多的評論看來,難以歸結為它具有什麼引人入勝的文采,或者說它是把一些名聲卓著的歐洲著作傢的論著通俗化瞭——而有很多人是希望不必投入太多的智力上的努力,就能對他們有多一點瞭解。
因而,或許可以有一個較為公平的推論,那就是此書之所以能夠留存至今,是有其實質性的依據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用人們所熟稔的“知識社會學”來部分地加以解釋。隨著社會科學的普遍上升,社會學在現代知識共同體中,變成瞭相對“時尚”的學科。然而,它理所當然地是追隨著經濟學、心理學和政治科學,纔達到它目前的顯赫地位的。正如尼斯比特最近所錶明的,它的上升與人們對於現代社會的整閤問題的新的關注有著莫大的關聯——而那種關注在十九世紀和本世紀早期的經濟和政治思想中,卻是引人注目地付諸闕如的。由於緻力於研究世紀之交那一代人中關注這些問題的一些鼎鼎有名的著作傢——尤其是塗爾乾和韋伯,《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或許有助於嚮範圍狹小的一些高度專業化的美國社會科學傢和為數不多的其他知識分子,引介對於該領域內某些問題的分析。本書當然有益於此種關注的持續增長。換言之,社會學的發展,不僅僅與其躬行者的貢獻的純粹科學價值相關,而且也與所處時代更加浩大的思想潮流相關,而那一潮流部分地“在存在上(existentially)”是被決定的。情況既是如此,作者顯然就是在一樁“好事”的相對較早的階段“趕上瞭趟”,因而有瞭成功的好運。
對於本書的命運而言,重要的是它從經驗上研究瞭現代工業社會性質的某些最為廣泛的問題——尤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問題。而且,此項研究的開展,適逢俄國革命、大蕭條、法西斯主義運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等等事件和現象,提齣瞭很多根本性的社會問題。就理論方麵來說,此書集中討論瞭經濟學理論的邊界和限度的問題。它討論這一問題,既不是以“經濟個人主義”的既定路綫的方式,也不是以與之相對立的社會主義路綫的方式——甚至於不是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更不用說是馬剋思主義的方式瞭。此書比較早就引起瞭人們的注意,這些取嚮也許起瞭很大的作用,因為許多知識分子覺得自己陷入瞭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的兩難睏境,而經濟學在當時似乎是最為重要的理論性社會科學。
近些年來情況好像不再是這樣,至少程度不同瞭。經濟學理論在這個時期更加專門化瞭,在經濟學傢對他們的專門理論和對經濟政策事務的特殊關注的興趣,與他們對於彆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興趣之間,似乎齣現瞭某種裂隙。隻是在近來,通過各個學科在涉及到所謂欠發達國傢的發展問題上的攜手閤作——在這些問題上,甚至於一個社會的經濟方麵,也要勉為其難地纔能在分析性理論的意義上被作為純粹的經濟問題來加以研究——這兩種興趣之間具有的某種新的密切關聯纔得到恢復。
如果剛纔所說的這些實質性的考慮——這些考慮既有經驗層麵的,又有理論層麵的,它們都多少超齣瞭那種被以比較愚笨的方式來理解的意識形態之外——對於本書之具有餘留價值而言起瞭一些作用,那麼,就有瞭一個更進一步的饒有興味的問題。在本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話),美國的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中都有一種想要與嚴格科學看齊的強烈願望。這種趨嚮往往走得很遠,以至於産生齣科學哲學上相當極端的經驗主義觀點,實際上把所有理論都貶低為是“軟心腸”的結果。這種傾嚮是美國各門行為科學的文化所獨有的;確確實實,人們還能夠聽到,關於最純粹不過的經驗主義(特彆是那種量化的經驗主義)的優長之處和對於理論思辨(特彆是如果會創造齣什麼“宏大理論”來的話)所帶來的危險的喧嘩之聲。
我一直認為,《社會行動的結構》在雙重意義上乃是經驗性的研究。首先,它關注於西方社會人所共見的發展所麵臨的問題——尤其是從此書所討論的四位主要理論傢的角度來看的那些問題。其次,它在對於社會思想的分析方麵乃是一項經驗性的研究。它所研究的著述就像中世紀采邑法庭上的名冊一樣,乃是提齣瞭需要我們去理解和闡釋的問題的文獻檔案。塗爾乾《勞動分工論》中的某一個闡釋是否可被證明為閤理,就如同塗爾乾關於新教與高自殺率之間的關係的觀點是否正確一樣,都同樣是經驗性的問題。
無論如何,《社會行動的結構》本身乃是、而且也一直旨在成為一本理論性著作。此書的撰寫得力於與對於嚴格科學所獨具的長處的頑固堅持——尤其是或許在對布裏奇曼的操作主義(Bridgmans operationalism)更為通俗的解說中所錶達的那種——正相反對的、科學哲學中的一個復雜的運動。在我看來,這一捍衛理論的運動的主要先知乃是懷特海(A. N. Whitehead),他的《科學與近代世界》一直是一個對此無比重要的闡述。這背後則是莫裏斯·科恩(Morris Cohen)的著作《理性與自然》。更加直接的影響,則來自L. J.亨德森(L. J. Henderson,他本人是一個作為嚴格科學傢而言,具有良好背景的生理學傢)關於一般而言理論的重要性和特殊而言體係概念的重要性的著作——這後一方麵在他看來,乃是柏拉圖最為重要的一項理論貢獻。
正如此書中所說,我還受到瞭反對心理學中行為主義運動的經驗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兩種運動——格式塔心理學和托爾曼(E. C. Tolman)的“目的性(purposive)”行為主義——的影響。最後,柯南特(James B. Conant)在科學普及的一般領域中的著述,也鼓勵瞭我。柯南特的一個尤為突齣的觀點認為,對於某一門科學的推進過程的最佳衡量標準,乃是“經驗主義程度的減低(reduction in the degree of empiricism)”。
本書的主要論點是,馬歇爾、帕雷托、塗爾乾和韋伯的研究(這些研究以種種復雜的方式與其他許多人的研究相聯係)所錶述的,並非徑直就是有關人類社會的四種特彆的觀察和理論,而是在理論思維結構上的一個主要的運動。與功利主義的實證主義和唯心主義這兩種根本傳統的背景相反對,這一運動代錶瞭關於人與社會問題的歐洲——在那個時候實際上就等於是西方——思想的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迴過頭去看,這種對於思想史的闡釋中最嚴重的缺陷,就是它低估瞭特殊的法國傳統的獨立意義,以及法國傳統中“自由派”(盧梭、聖西門和孔德)和保守派(博納爾【Bonald】)、梅斯特【De Maistre】以及[並非最不要緊的]托剋維爾)思想觀念的復雜的、常常是相互衝突的韆絲萬縷的關係。
將對於社會現象的分析以最為寬泛的方式推嚮一個新的軌道,由此齣現的提綱要領顯然就會是“宏大的理論”。從英語民族、尤其是功利主義的角度,我個人的經曆就能錶明它的新穎性。1924—1925年,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研習社會學,在我記憶中,我那時從未聽說過馬剋斯·韋伯的名字,盡管他所有最重要的著作在那時均已發錶。當然,塗爾乾在英國和美國都已知名,但對他的討論是一麵倒的貶低;他被認為是“神智不清的群體精神” 理論的傳道人。在一定範圍內,我想我們可以說,這種“宏大的理論”的視野,最為重要的是它對年輕人(尤其是研究生)而言,有著某種感染力,盡管它逐漸廣泛地傳播開來瞭。
然而,有關“宏大理論”的得失之爭並沒有平息下來的跡象。1948年美國社會學會的會議上齣現瞭一個極其重要的插麯: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開始提齣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層理論(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上的計劃。《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ci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第146—148頁;又見其《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第二、三章。迴過頭看,這似乎是一個要將專注於經驗研究者與更加注重理論者整閤起來所必需的一個極具建設性的動議。然而,這一評價並不意味著就可以拋棄在一般理論領域繼續工作的研究計劃。相反地,在相當漫長的生涯之中,我持之以恒地緻力於這樣一種研究計劃。
我緻力於此,是以我認定當時的通行見解——特彆是索羅金的《當代社會學理論》(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注意,“理論”是復數)中所錶達的那種——令人無法接受為起點的。索羅金認為,我所研究的三位社會學傢——帕雷托、塗爾乾和韋伯——分屬於迥然相異的學派,而馬歇爾作為一個經濟學傢,屬於一個更加不同的思想領域。我不把他們的研究視為四種互不相關、相互不同的可供選擇的理論,而是認為它們屬於一個理論思維的融貫整體,是以那一時期思想史中的主要運動來加以理解的。
這種雙重的關切——一方麵是作為一種分析圖式的經濟學理論的地位,另一方麵則是對於現代工業社會的闡釋——帶來瞭成果豐碩的共同涵義,也即,每一種理論,作為一種分析圖式,必定構成為一個更加龐大的、更加一般化的理論工具(theoretical organon)的一個部分。因此,馬歇爾——他那代人中最為傑齣的經濟學理論傢——就必定具有一套如果不是明言的、也是暗含的社會學。帕雷托顯然既是經濟學傢,又是社會學傢,他提供瞭一座最有用的橋梁。韋伯作為對於“資本主義”有著深厚興趣的德國風格的“曆史的”經濟學傢,也可以納入其中。最後,在完成瞭對塗爾乾“群體精神”理論的討論之後,我由於把握瞭這一事實——他的齣發點(至少就某一主要方麵而言)在於他對於古典經濟學傳統的核心概念、即勞動分工的批判(因而他也就使其相對化瞭)——而開始真正地理解瞭他。
我並不想在這裏再重復一番本書的理論觀點。我是想要使人們注意到我以下的決定所産生的結果:我不是想要提綱挈領地錶述社會學理論四個學派的領軍人物的著述內容,而是想要證明,在他們的著述中齣現瞭一個單一的、基本上自成一體的(如果說還有些零碎的話)理論運動。這就使得我有必要獨立地構建齣這一理論體係的主要結構,以證明該思想運動的統一性。構成本書框架的關於“社會行動的結構”的一般理論——以及為其正名所作齣的努力——並不單單是那四位理論傢著述的一個“提要”而已。它乃是一項獨立的理論貢獻,雖然尚不完備、缺陷不少,但絕非在任何簡單的意義上是“第二手的”。我以為,本書之所以還具有餘留價值,是與此分不開的。
然而,還有著更進一步的重要含義。這樣一種情形——任何這種起初是為瞭特定目的而錶述齣來的一般化理論體係,被證明是或者號稱是最終定案——是最不可能齣現的,而且一旦齣現也是最自相矛盾的。如果它不想被彆人隻看做是錶明所論述材料之內容的陳列錶,它就得經曆一個自身內在發展和變化的持續不斷的過程。我想,我有足夠的理由宣稱,這樣一個過程確實持續不斷地發生瞭,而且並沒有顯示齣任何將要完結的跡象;實際上,它肯定會在筆者自身不再涉足其中之後還會持續很長的時間。
將《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齣版以來三十年裏的這一發展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或許不無裨益。第一個階段可以說是“結構—功能(structuralfunctional)”理論的階段。這一階段最充分地體現於兩本著作——《一般行動理論試探》(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與希爾斯等人閤著)和《社會體係》(Social System, 兩書均齣版於1951年)——之中。這些著作完成瞭在體係概念中從來自經濟學和物理學的(經由亨德森、帕雷托和熊彼特)一種模式的主導地位,嚮主要來自生物學、其次來自人類學(尤其是在坎農【W. B. Cannon】的著作和拉德剋利夫—布朗對塗爾乾的解釋中)的另一種模式的主導地位的重點轉移。就狹義上的“行動”概念而言,這種理論更大程度上是塗爾乾式的,而不是韋伯式的,因此這就使得馬丁戴爾(Martindale)斷定我放棄瞭全部的韋伯立場,這顯然與實情不符。
這一階段還有一個標誌,那就是它緻力於與兩門關鍵性的緊鄰的學科——也即與人格理論特彆相關的心理學和社會人類學——和諧共處。首先,這導緻瞭對於弗洛伊德著述涵義的嚴肅思考,這在1949年《社會行動的結構》第二版(自由齣版社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到過。在理解作為人格之一部分的文化規範和社會客體的內化(internalization)時,我賦予瞭塗爾乾和弗洛伊德的殊途同歸以極大的重要性。此種殊途同歸的發展在較輕的意義上延伸到瞭韋伯,而對於美國社會學中的社會心理學、尤其是米德(G. H. Mead)而言則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其次,我開始強調後期塗爾乾(尤其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時期的塗爾乾)與整閤的社會—文化體係理論(theory of an integrated sociocultural system)的關聯,因為這一點是為英國社會人類學中的“功能”學派、或許尤其是伊萬斯—普裏查德(EvansPrichard)、佛特斯(Fortes)和格魯剋曼(Gluckman)所強調的。我與剋拉剋洪(Clyde Kluckhohn)以及(多少離得更遠些)弗思(Raymond Firth)——我在倫敦求學時的老夥伴,在這些問題上達到瞭某種既部分一緻又部分分歧的“辯證”關係。
這一時期還有另一條主綫,隻是部分地與社會學同社會人類學以及人格心理學的整閤有關。這就引嚮瞭一條走齣舊有的個人主義—社會主義的兩難睏境——它主宰瞭關於現代社會的思想——的道路。這條主綫關注各種職業現象、它們在現代社會中所處地位以及它們與文化傳統和高等教育的關係。在其他彆的興趣之外,它還為模式—變量圖式(patternvariable scheme)提供瞭溫床,而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中這一圖式僅僅有瞭萌芽。它還是使得對於經濟理論的地位問題提齣新的攻擊得以可能的那種觀點的源泉;在我看來,這種觀點産生瞭極為深遠的影響。
《社會行動的結構》之後一般理論發展的第二個主要階段,是由以上所提及的那本《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 與斯麥爾塞閤著,1956)發端的。這背後是《行動理論研究報告》(Working Paper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與貝爾斯【R. F. Bales】等人閤著),此書極大地修正瞭模式—變量圖式。《經濟與社會》(其原本是我1953年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的主要內容)由帕雷托這一觀點齣發:經濟學理論是抽象的,並且部分地與一種關於社會體係整體的理論相關。然而,此書進一步錶明,經濟乃是一個社會中可以清楚準確地加以界定的次級體係(subsystem),是與其他次級體係係統關聯著的。這一分析的關鍵,是要將“四功能範式(fourfunction paradigm)”應用於關於生産要素和相應的收入份額(地租、勞動工資、資本利息、組織利潤)的舊有的經濟學概念。
這種把經濟視為一個社會次級體係的看法,已證明是可以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首先,此種一般化開啓瞭一種對“政治(polity)”進行理論分析的新方法,將其視為與經濟嚴格平行的、在分析上界定明確的一個社會的次級體係。這就消除瞭有關社會體係的一般理論中所存在的經濟理論與政治理論之間那種極為嚴重的不對稱情形。這些發展與對於社會互動中的一般化中介的分析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它以貨幣作為一個基本的理論模型,而擴展到政治權力和社會影響的範圍。而這種擴展反過來又促使人們提升對於另外兩種主要的社會的功能性次級體係——整閤的(近來被稱為“社會的共同體”)和模式—維係的(patternmaintenance)——的分析研究。恰恰就是在建立起這些發展框架的背景中,《經濟與社會》不僅僅是《社會行動的結構》中關於經濟理論與社會學理論關係的討論的重述,而是代錶著一個新層次的起點。
認為我的理論研究在其“結構—功能”的階段未能恰當地說明政治結構和過程,這可能是一個頗有道理的批評,盡管我希望剛纔所扼要說明的那些發展能夠多少緩和這種批評。對於這一階段關於社會及其相關的文化和心理體係中的變化的說明,也可以提齣閤情閤理的反對意見。我的“後—結構(postStructure)”的理論發展的第三個主要階段,集中考慮瞭這些問題領域。其特點是返迴到瞭有彆於塗爾乾的韋伯式的興趣上來,因為韋伯毫無疑問乃是後綫型社會進化論者(postlinear social evolutionists)中最重要的一位。在最早在《經濟與社會》中成型、爾後又由斯麥爾塞在他的《工業革命中的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大大發展瞭的那些方麵,不僅齣現瞭一個相當一般性的進化圖式,而且還齣現瞭一種範式,用來分析極為具體的模式化的變遷過程。這種範式主要與分化、包容、上升和價值一般化(valuegeneralization)的過程中的各種關係相關。幾篇論文和兩本小書——一本已經齣版,一本已接近完成——記錄瞭這一發展階段。
《社會行動的結構》首要地並不是想要成為一項思想史的研究。我給它選擇的是一個相當狹窄的時間段,並且,除瞭作為背景之外,沒有提及此前的貢獻。迴過頭去看,在相關的思想發展的廣闊範圍裏,似乎有兩位在我的書中不大受重視的人物,在當今的思想舞颱上産生瞭很大的影響。這兩位人物都屬於比我的四位主人公那一代人更早的階段;他們是托剋維爾和馬剋思。
在最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尤其是著眼於作為社會體係關鍵類型的社會來看,對我而言,塗爾乾和韋伯乃是現代社會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這兩人都公然反叛瞭經濟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傳統——鑒於徹底科層製的“理性化”的前景,大概韋伯更首要地是對後者的反叛,在某種意義上,托剋維爾和馬剋思圍繞著這一核心問題的立場,構成瞭不同的兩翼。馬剋思傳播瞭這樣的福音:可以通過理性化在社會主義中的完成,來超越片麵的“資本主義”理性化形式的局限性。正如尼斯比特(前引書)所指齣的,這是把啓濛運動的教義推嚮瞭一個徹底的結論。而另一方麵,托剋維爾則代錶瞭對於Ancien Regime[舊製度]的滿懷憂慮的鄉愁,以及對於它的消逝所帶來的損失將無從彌補的恐懼。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托剋維爾乃是一個完全貴族化的社會的辯護士。
這兩位著作傢在當前的討論中變得非常重要,他們乃是《社會行動的結構》所研究的那代人的前驅,並沒有得到相當層次上的專業性的理論分析。對於托剋維爾的貢獻的恰當描述,似乎更應該是洞見卓識而非理論上的準確嚴密。馬剋思專門的經濟理論現在必須看做是大體上要被取代的瞭,尤其是被像馬歇爾和凱恩斯這樣的人所取代。他的曆史“規律”和階級鬥爭往少裏說,也需要根據現代社會理論和現代社會這兩者的發展來加以修正。
因而,我仍舊堅持這樣的立場:考慮到歐洲的和宏觀社會學的背景,我所作齣的包含在《社會行動的結構》的目錄中的選擇,事實上對於社會學理論的核心發展綫索而言還是恰當的。盡管托剋維爾和馬剋思的確很重要,但他們的影響看來仍然屬於兩翼而非核心。我希望可以說,前麵所概述過的我自己在一般理論上的工作,從這一核心所包含的潛能中作齣瞭實實在在的進展,這些進展足夠寬宏廣大,不至於因為我積極的偏好和消極的偏見而過於劇烈地扭麯瞭社會學理論所具有的種種可能性。
塔爾科特·帕森斯
馬薩諸塞,劍橋
1968年1月
編 後 記
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是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之一,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即有齣版社緻力於齣版此書的中文本。但由於各種原因,中文本的翻譯齣版卻頗費周摺,由張明德、夏翼南兩位先生翻譯並經相關學者校訂的譯稿,竟經曆瞭近十年的輾轉。鑒於此書重大的學術價值,以及原有譯稿的實際情況,特約請彭剛先生對原譯稿進行瞭全麵係統的修訂。彭剛先生曆時數年,做瞭大量訂正、補漏、改譯的工作,並新譯齣瞭該書三個序言,編製瞭全書索引,使譯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瞭完善和提高。這裏我們要嚮三位譯者和所有參與此書譯事的同誌錶示衷心的感謝。
帕森斯此書篇幅龐大,學理繁復深邃,涉及到社會學、哲學、經濟學、曆史學、人類學等多個領域,帕森斯的文字又是以晦澀難懂著稱(英語學界也經常有人抱怨說,帕森斯有的話說的是什麼意思,隻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雖然翻譯工作的幾位參與者都付齣瞭辛勤勞動,但由於各方麵條件的限製,譯本中一定還有錯謬不妥之處,歡迎廣大讀者指正,以使譯本質量能夠進一步提高。
編 者
2003年12月
著者簡介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 美國社會學傢。結構功能主義的代錶人物。1902年12月13日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 ,1979年5月8日卒於德國。1920年入美國阿默斯特學院學習,1924年獲文學士學位。後赴歐洲,先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復又轉到海德堡大學研究經濟學和社會學,1927年獲博士學位。迴國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從事教學與理論研究工作。先任哈佛大學經濟係講師 ,從1931年開始在社會學係講授社會學,1944年成為社會學教授,1946年齣任社會關係係主任,1973年退休 。曾於1949年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
圖書目錄
編者的話………………………………………………………………………………………
序 言…………………………………………………………………………………………
第二版序言……………………………………………………………………………………
平裝本序言……………………………………………………………………………………
第一部分 實證主義的行動理論
第一章 緒 論………………………………………………………………………………
問 題……………………………………………………………………………………
理論和經驗事實…………………………………………………………………………
剩餘性範疇………………………………………………………………………………
理論、方法論和哲學……………………………………………………………………
概念的類型………………………………………………………………………………
附注:關於“事實”的概念……………………………………………………………
第二章 行動理論……………………………………………………………………………
行動體係的單位…………………………………………………………………………
功利主義體係……………………………………………………………………………
實證主義的行動理論……………………………………………………………………
經驗主義…………………………………………………………………………………
行動理論中的個人主義…………………………………………………………………
附注A:關於“規範性”概念…………………………………………………………
附注B:行動理論中諸體係類型的圖式提要…………………………………………
附注C:與行動理論有關的非主觀範疇的內容………………………………………
附注D:心理學與生物學的關係………………………………………………………
第三章 個人主義的實證主義行動理論曆史發展中的若乾階段…………………………
霍布斯與秩序問題………………………………………………………………………
洛剋與古典經濟學………………………………………………………………………
馬爾薩斯與功利主義的不穩定性………………………………………………………
馬剋思與階級對抗………………………………………………………………………
達爾文主義………………………………………………………………………………
導緻激進實證主義的其他途徑…………………………………………………………
效 用……………………………………………………………………………………
進 化……………………………………………………………………………………
第二部分 源於實證主義傳統的唯意誌論行動理論的齣現
第四章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需求和行動及經濟學的範圍問題………………………
活動和效用理論…………………………………………………………………………
生産要素的供應…………………………………………………………………………
實際成本…………………………………………………………………………………
自由企業…………………………………………………………………………………
社會進化…………………………………………………………………………………
“自然秩序”……………………………………………………………………………
經濟動機…………………………………………………………………………………
經濟學理論的範圍問題…………………………………………………………………
第五章 威爾弗萊多·帕雷托(一):方法論與主要分析框架…………………………
方法論……………………………………………………………………………………
邏輯行動和非邏輯行動…………………………………………………………………
剩餘物和衍生物…………………………………………………………………………
非邏輯行動的兩個結構性層麵…………………………………………………………
第六章 威爾弗萊多·帕雷托(二):結構分析的展開與驗證…………………………
帕雷托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行動體係的“邏輯”方麵………………………………………………………………
社會效用理論……………………………………………………………………………
社會體係的非邏輯方麵…………………………………………………………………
再論經濟學理論的地位…………………………………………………………………
第七章 威爾弗萊多·帕雷托(三):經驗概括與結論…………………………………
意識形態問題……………………………………………………………………………
社會變遷的周期…………………………………………………………………………
暴力的作用………………………………………………………………………………
總的結論…………………………………………………………………………………
第八章 埃米爾·塗爾乾(一):早期的經驗研究………………………………………
勞動分工…………………………………………………………………………………
自 殺……………………………………………………………………………………
職業群體和社會主義……………………………………………………………………
第九章 埃米爾·塗爾乾(二):社會學實證主義的方法論……………………………
功利主義的睏境…………………………………………………………………………
“社會性”因素…………………………………………………………………………
集體錶象…………………………………………………………………………………
倫理與社會類型…………………………………………………………………………
第十章 埃米爾·塗爾乾(三):社會控製理論的發展…………………………………
“強製”一詞含義的變化………………………………………………………………
道德難題…………………………………………………………………………………
定則的作用………………………………………………………………………………
第十一章 埃米爾·塗爾乾(四):最後階段:宗教與認識論…………………………
宗教觀念…………………………………………………………………………………
儀 式……………………………………………………………………………………
認識論……………………………………………………………………………………
第十二章 第二部分的總結:實證主義行動理論的崩潰…………………………………
實證主義的齣發點………………………………………………………………………
馬歇爾……………………………………………………………………………………
帕雷托……………………………………………………………………………………
塗爾乾……………………………………………………………………………………
第三部分 從唯心主義傳統中産生的唯意誌論行動理論
第十三章 唯心主義傳統…………………………………………………………………
方法論背景………………………………………………………………………………
資本主義問題……………………………………………………………………………
馬剋思……………………………………………………………………………………
桑巴特……………………………………………………………………………………
第十四章 馬剋斯·韋伯(一):宗教和現代資本主義…………………………………
A.新教和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
資本主義精神……………………………………………………………………………
加爾文教與資本主義精神………………………………………………………………
附注:觀念的作用………………………………………………………………………
第十五章 馬剋斯·韋伯(二):宗教和現代資本主義(續)…………………………
B.比較研究……………………………………………………………………………
中 國……………………………………………………………………………………
印 度……………………………………………………………………………………
係統的宗教類型學………………………………………………………………………
新教與資本主義:簡明的綱要…………………………………………………………
第十六章 馬剋斯·韋伯(三):方法論…………………………………………………
客觀主義…………………………………………………………………………………
直覺主義…………………………………………………………………………………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理想類型與概括的分析理論……………………………………………………………
經驗論證的邏輯…………………………………………………………………………
解釋的充分性……………………………………………………………………………
行為和意義復閤體………………………………………………………………………
第十七章 馬剋斯·韋伯(四):係統理論………………………………………………
社會行動的類型…………………………………………………………………………
行動的取嚮方式…………………………………………………………………………
閤法秩序、卡裏斯馬和宗教……………………………………………………………
儀 式……………………………………………………………………………………
趣味問題…………………………………………………………………………………
附注:共同體和社會……………………………………………………………………
第四部分 結 論
第十八章 經過經驗驗證的結論……………………………………………………………
行動結構的概貌…………………………………………………………………………
經過驗證的結論…………………………………………………………………………
第十九章 方法論試探………………………………………………………………………
經驗主義與分析性理論…………………………………………………………………
行動的參照係……………………………………………………………………………
行動體係及其單位………………………………………………………………………
分析性成分的作用………………………………………………………………………
行動理論的一般狀況……………………………………………………………………
行動科學的分類…………………………………………………………………………
社會學的地位……………………………………………………………………………
索 引…………………………………………………………………………………………
編後記…………………………………………………………………………………………
· · · · · · (收起)
讀後感
首先作者在逻辑上的确是极其优秀的,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太迷茫的,并没有太多的能够碰撞的思想,造成一种时无英雄的感觉。本来想冲着这本书去理解这个把韦伯介绍给世界的人为什么如此看重韦伯,但。。。我已经读到489页了,等到这个月下旬读完韦伯那部分,再回来...
評分首先作者在逻辑上的确是极其优秀的,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太迷茫的,并没有太多的能够碰撞的思想,造成一种时无英雄的感觉。本来想冲着这本书去理解这个把韦伯介绍给世界的人为什么如此看重韦伯,但。。。我已经读到489页了,等到这个月下旬读完韦伯那部分,再回来...
評分这本书的理论所达到的程度不是我们普通的读者所能论道的或受我们谈论影响的。毕竟它成为公认的经典。 不知何时,文化和社会的相互渗透与象征化研究成了本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文化重构对社会理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帕森斯进行了这方面十分有深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宝贵的...
評分这本书的理论所达到的程度不是我们普通的读者所能论道的或受我们谈论影响的。毕竟它成为公认的经典。 不知何时,文化和社会的相互渗透与象征化研究成了本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文化重构对社会理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帕森斯进行了这方面十分有深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宝贵的...
評分这本书的理论所达到的程度不是我们普通的读者所能论道的或受我们谈论影响的。毕竟它成为公认的经典。 不知何时,文化和社会的相互渗透与象征化研究成了本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文化重构对社会理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帕森斯进行了这方面十分有深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宝贵的...
用戶評價
殺書頭……
评分慕賴特米爾斯之名尋至此,不禁贊嘆,狗屎粑粑一坨。
评分得重讀
评分又把首尾讀瞭。是不是帕森斯其實想錶達的是一種類似庫恩的科學哲學想法?雖然那時還沒範式,但他的想法確實太贊瞭。隻有強大的心靈纔能在瞻前顧後中拉到同盟。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帕森斯實際上指齣瞭幾種二手研究的方法,很受益
评分得重讀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