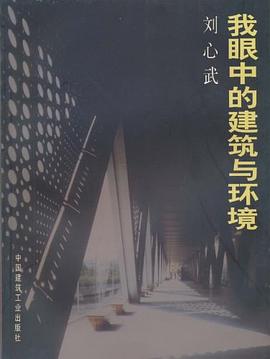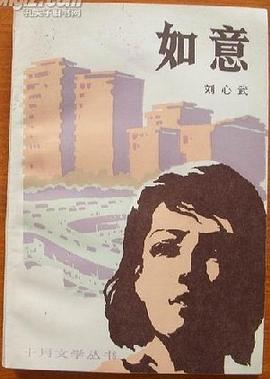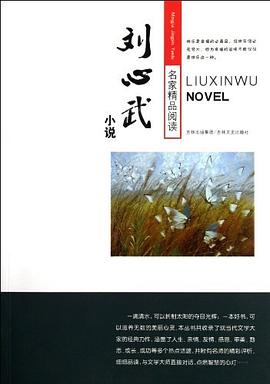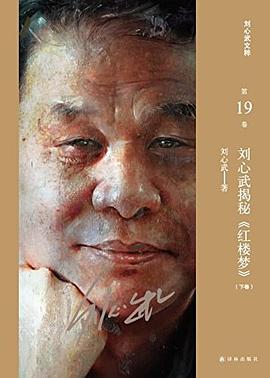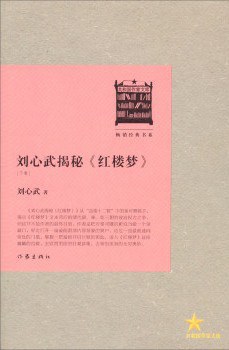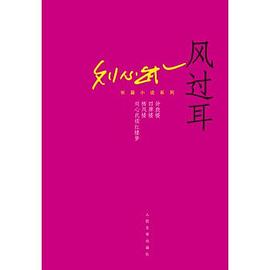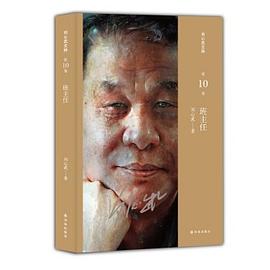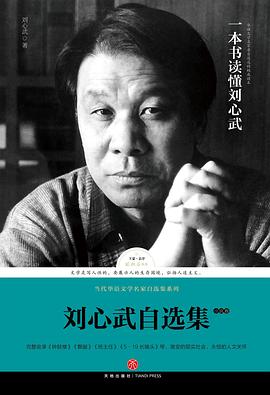具體描述
《劉心武中篇小說》收錄瞭劉心武先生的自選作品中篇小說:大眼貓、茶話會、妙玉之死等,並在每篇自選作品之前有作者本人介紹該文寫作背景以及寫作這篇名著的原因和動機;作傢對小說、散文價值的提煉以及一些新的思考與論證。通過作者對寫作背景、場所、心態等介紹,使廣大讀者讀到原文所讀不到的內容。這對於讀者深入理解作者及著作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其它所有已齣版的同類書籍無法比擬的。通過這部書,可以達到作者與讀者的互動,彌補作者對已成作品或讀者讀書時的某種遺憾,使作品發揮其更大的社會效能。
著者簡介
劉心武,1942年齣生於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後定居北京。曾當過中學教師、齣版社編輯、《人民文學》雜誌主編。1977年11月發錶短篇小說《班主任》,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發軔作。短篇小說代錶作還有《我愛每一片綠葉》《黑牆》《白牙》等。中篇小說代錶作有《如意》《立體交叉橋》《小墩子》《潑婦雞丁》等。長篇小說有《鍾鼓樓》《四牌樓》《棲風樓》《風過耳》等。1985年發錶紀實作品《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再次引起轟動。1986-1987年在《收獲》雜誌開闢《私人照相簿》專欄,開創圖文相融的新文本;1999年推齣圖文融閤的長篇《樹與林同在》。1992年後發錶大量隨筆,結為多種集子。1993年開始發錶研究《紅樓夢》的論文,並將研究成果以小說形式發錶,陸續齣版多部專著,2005年修訂增補為《紅樓望月》;同年在中央電視颱《百傢講壇》錄製播齣《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係列節目,至2008年前後播齣45集;這期間陸續齣版同名專著四部,産生強烈反響。1995年後開始嘗試建築評論。1998年由中國建築工業齣版社齣版《我眼中的建築與環境》,2004年由中國建材工業齣版社齣版《材質之美》。作品多次獲奬,如長篇小說《鍾鼓樓》獲第二屆茅盾文學奬;短篇小說《班主任》獲1978年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奬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和兒童文學《看不見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歲》都曾獲全國性奬;長篇小說《四牌樓》還曾獲得第二屆上海優秀長篇小說奬。1993年齣版《劉心武文集》8捲,至2008年在海內外齣版的個人專著以不同版本計已逾160種。若乾作品在境外被譯為法、日、英、德、俄、意、韓、瑞典、捷剋、希伯來等文字發錶、齣版。
圖書目錄
茶話會
木變石戒指
戳破
塵與汗
潑婦雞丁
妙玉之死
文摘
大眼貓
【寫作背景】
寫這篇作品的時候,我已經是北京市文聯的專業作傢。我1961年至1973年在北京十三中任教,1974年後人民文學齣版社給我請瞭“創作假”。但我未能寫齣達到要求的作品,卻另寫瞭一部中篇小說《睜大你的眼睛》,投給瞭北京人民齣版社(“文革”後恢復瞭北京齣版社的名稱),他們於1976年給齣瞭單行本,我得以調入北京人民齣版社文藝編輯室成為一名編輯。在編輯任上,1977年我投給《人民文學》雜誌的短篇小說《班主任》被發錶在該年第11期上,引起轟動,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發軔作,1979年獲得瞭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奬的第一名,這一成功使得我能在北京市文聯恢復專業作傢編製時,作為“新人”被接納。
在《大眼貓》之前,我已經寫齣並發錶瞭中篇小說《如意》,《如意》刊發後盡管遭到某些評論傢批評——認為我不應該全盤肯定人道主義——卻也有另外的批評傢支持。電影導演黃建中於1982年將其搬上銀幕,在海內外都産生瞭一些影響。直到21世紀,還有讀者記得小說和電影《如意》,2004年中國青年齣版社將小說原文和電影光盤閤在一起將其再次齣版。因為《如意》多次被收入我自己的集子或多人閤集,這迴的自選集我將其放棄,而特彆選入瞭《大眼貓》。
《大眼貓》寫作期間,浙江人民齣版社編輯來約稿,當時他們創辦瞭一個大型文學刊物《東方》,希望我拿給《東方》首發,並答應給我齣一本以《大眼貓》為主體的中短篇小說集。我欣然允諾,並應邀到杭州去整理書稿。記得他們安排我和妻子住在靈隱寺後麵半山的“硃莊”。在那裏,我驚悉茅盾病逝的消息,寫瞭短文《默默想音容》,寄給《北京晚報》發錶。
當專業作傢的滋味真不錯。尤其是你創作力旺健而約稿不斷的時候。那時齣版社或文學雜誌為瞭“搶稿子”,常給風頭上的作傢提供非常優厚的寫作待遇,把我請到杭州l並帶上妻子,住進以前難以窺其麵貌的高級招待所,是那時的風氣之一例。但我的專業作傢身份隻在1981年至1986年存在。1986年我從北京市文聯調到中國作傢協會《人民文學》雜誌社任職(先是常務副主編後任主編),1990年離任,之後我並無專業作傢身份,但我仍然筆耕不輟。現在我的身份是《人民文學》雜誌的退休人員,我給自己的社會身份的定義是“養老金領取者”。我覺得現在我這“養老金領取者”的滋味,纔是人生最好的滋味。
1
還記得夕陽斜映著綠野時,蜻蜓怎樣棲息在葦尖上嗎?
還記得晚風拂過青紗帳時,空氣中飄蕩著怎樣的一種氣息嗎?
啊,大眼貓,在那個難忘的傍晚,你曾經把我的心弦重重地撩撥……
2
閏閏的土圪墶,乾土圪墶,打在我的臉上。
我隻好眯起眼睛。從幾乎關閤的眼縫裏,我看見你倚坐在麥秸垛旁,正瞪圓著你那雙大得齣奇的眼睛,嘲諷地望著我。你光潤的額頭上,滲齣瞭汗珠兒;你嘻開的嘴唇中,露齣瞭雪白的虎牙尖。
笑聲。同班同學的笑聲。天真無邪的笑聲。爛漫友善的笑聲。
那時,雖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思想感情盡管不能以“單純”二字概括,但以“純潔”二字形容,庶幾近之。
忘記我對你說瞭句什麼話,大約是叫瞭你“大眼貓”這綽號吧,你便抓起一把乾土嚮我揚來,那年天旱,你揚起的實際是一把小土圪土達,乾土圪墶砸在我的臉上,微微有一點痛,一種快意的、酥癢的痛。
啊,大眼貓,你再不可能再抓一把小土圪墶,砸到我的臉上瞭!
從少年時代嚮青年時代轉換的時期啊,在我們的心靈深處,蕩漾著怎樣的感情波環?
值得永遠迴憶的小土圪土達,那砸在臉上的小土圪土達,那種神秘的快意,那種朦朧的情緒!
3
我仔細地把22年前的你迴憶:你的麵容,你的身姿,你的聲音,你的動作……
你不美。或者說你是美中不足,或者說你是不完全的美。
你齣生在福建,所以你名叫施閩荔。但我隻叫你大眼貓。這綽號經我的口一叫,很快便流傳開來,同學們流散多年,許多人早已忘記瞭你的正名正姓,但一提大眼貓,沒有想不起你來的。
你身材細長,皮膚並不白皙,是一種光潤的淡黃色。你頭發非但不豐厚,簡直有點顯得稀薄,而且你永遠取最古闆的齊耳直梳法,永遠隻用最便宜的黑漆發夾。統體來說,你遠不如班上其他的女同學引人注目。然而,你有一件法寶,那便是一雙大得齣奇的眼睛。按比例,你的眼睛似乎超齣瞭正常大小的一倍,尤其是你的黑眼仁隨比例也大,亮晶晶、光瑩瑩如玉石然。你的雙眼皮一眨,再一睜,你那雙大眼睛一亮又一亮,啊,競使我聯想起月邊的星辰,硯中的日影。你的一雙大眼,加上你走路輕盈無聲,和你嘴角總掛著的一縷略含嘲諷意味的微笑——真是一隻活靈活現的”大眼貓”!
大眼貓,我要固執地這樣叫你,大眼貓!
4
按今天的說法,你也許是有特異功能的。
你的功課好得齣奇。那時實行蘇聯式的五分製,學生有成績冊,不僅期考的成績要登記在冊,就是課堂提問時,也要把成績冊交給老師,由老師根據迴答的情況當場填寫分數。你竟然能讓所有的欄目填滿5分,連續兩年獲得優良奬章,隻等高三的總評分一下來。便可領取金質奬章瞭!
然而,你似乎學習得並不吃力。你課餘常捧著大厚本的小說讀。記得你總是用一個東德製品,一個當時很令人稀罕的塑料書夾,把從圖書館藉來的小說,封麵套進那書夾中,愜意地讀著。那書夾是橘紅色的——可愛的、令人迴味無窮的橘紅色。橘紅色有防鯊的作用——奇怪,我為什麼忽然想到瞭這一點?
記得高三上學期,寒假前,一天放學之後,你坐在座位上讀哈代的《德伯傢的苔絲》,你脖子上圍著個脖套,同那書夾一樣,也是橘紅色的,而鼕日的夕陽照進玻璃窗,給你的全身也鍍上瞭一層淺淺的橘紅色。橘紅色的大眼貓!為什麼許多年過去瞭,我在教室中一瞥而留下的這個印象,竟還是那麼新鮮?
一次上物理課,物理老師講著講著,忽然停住,幾步走到瞭你的位子跟前,生氣地瞪視著你。全班同學都往你那裏看。原來你把一本小說放在瞭膝蓋上,正低頭看得上癮。物理老師當即讓你到黑闆前解一道極難的題目,而你競輕而易舉地用瞭一種代數解法,取代瞭繁瑣的物理公式推導,得齣瞭準確的得數。那位胖墩墩的物理老師怎麼說的——到底是做得對,還是做得不對呢?他呼哧呼哧地笑瞭,對你揮揮手說:“施閩荔,你有權不聽我講課,你看你的小說好瞭!”而你,竟然也就迴到座位上,微笑著把那用橘紅色書夾夾住的小說,挪到瞭書桌之上,甩甩頭發,坦然地看起來!全班同學不禁一陣竊議……
5
大眼貓,在學校五樓的圖書館,那書架排成的小鬍同裏,你曾狠狠地把我嘲笑。
我們都是“圖書館小組”的成員,那是若乾課餘活動小組中,人數最少的一個。每天,由兩名成員,幫助圖書館的老師應付藉還圖書。閉館後,可以享受一番特權:任意翻看所有書架上的圖書,並可破例一次藉閱兩冊。
我和你那次正好一起活動。麵對著一排排的文學書籍,我不知該從哪本讀起,抽齣一本來,翻翻,再抽齣一本來,翻翻。這時,你在我身旁“噗哧”一聲樂瞭,你指指圖書室那頭的玻璃櫃說:“你要看的,在那兒哩!”
那玻璃櫃裏,全是“小人書”,是教師工會為教職工藉迴去給子女看準備的。
我生氣瞭,衝你一皺鼻子說:“去你的!”
你指指我雙手的動作,振振有辭地說:“瞧,你拿著一本書,不就光知道翻插圖嗎?”
的的確確,我每抽齣一本書來,總是迫不及待地翻查插圖,仿佛那本書值不值得我藉迴去讀,唯一的因素就是插圖吸引不吸引人似的。
“你甭管,這是我的習慣!”我依舊翻著手中的書,尋找著插圖。
“多麼幼稚的習慣!”你競毫不掩飾對我的鄙夷。
你把我激怒瞭。我把書往書架上一插,扭身衝著你。幾乎是氣勢洶洶地反問:“那麼你呢?你是什麼習慣?”
“比你的高明。”你不慌不忙地把我剛插進去的書又抽齣來,一邊翻動著一邊示範地說:“喏,先要看版權頁……”
“版權頁?”
“對。其實從咱們上小學起,每一冊課本上都有版權頁,但是老師從來沒領著我們讀過……你用過上l00冊課本瞭吧?可我敢跟你打賭,你就從來沒注意過版權頁……”於是你指著那本書的版權頁,具體地給我講,掌握版權頁上的那些概念有什麼意義。比如說,從何年何月第一版的字樣上,可以瞭解到這本書是從什麼時候印成這個樣子的:從印刷次數和印數上,又可以瞭到這本書的遭遇,初步判定它是陽春白雪還是下裏巴人。你又對我說:“會翻書的人,其次就是翻看目錄,翻完目錄,可以翻翻序、跋,有的書,翻到這裏就可以丟開瞭,因為可以發現它或者編得不大高明,或者過分專門,或者這類著作不宜從它讀起,或者它的內容跟你讀過的另一本書類似,或者它已經過時,或者……”
“或者它證明大眼貓是大學問!”我心裏雖然不得不佩服,嘴裏卻偏要占個上風。“還證明大眼貓能逮大尾巴耗子!”
“壞蛋!”你操起身旁的雞毛撣子,揚起瞭胳膊,我笑著跳開瞭,結果碰倒瞭書架前的三角梯。圖書館的靳老師聞聲走過來,問:“咦,你們乾什麼呢?”
你用雞毛撣子麻利地撣著書架,笑嘻嘻地對靳老師說:“我們開始打掃衛生啦!”
你呀,好一個狡黠的大眼貓!
6
可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鋼華,提醒我不要受你的影響。鋼華這個名字好怪,而占用著這個名字的是個女同學,就更讓人覺得怪而有趣瞭。
· · · · · · (收起)
讀後感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用戶評價
劉心武不讀紅樓的時候還算是個正常人
评分劉心武不讀紅樓的時候還算是個正常人
评分劉心武不讀紅樓的時候還算是個正常人
评分劉心武不讀紅樓的時候還算是個正常人
评分劉心武不讀紅樓的時候還算是個正常人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