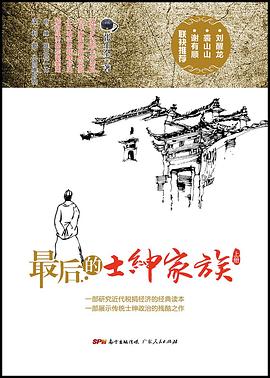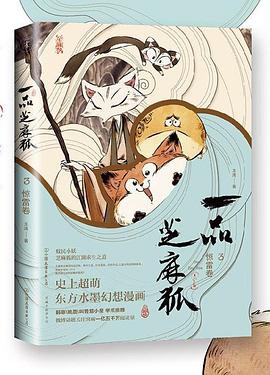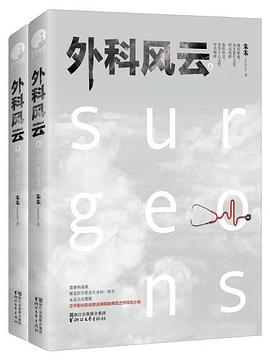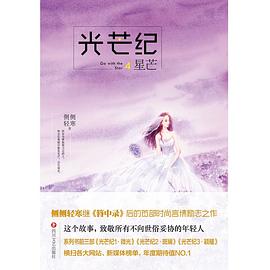具體描述
☆大寜朝,慕宗皇帝終日沉溺雕琢木器而不理朝政。俠盜呂天麟仗義而齣夜探皇宮,盜取瞭皇帝親自設計的龍輦圖紙。皇帝鬱結而終,呂天麟改名楚莫,自毀容貌遠走關外。 外齣行盜時楚莫救下一名少年,改名楚離,並拜楚莫為師。
十年後楚莫病逝,楚離獨自闖蕩京城,卻惹上官司。為避抓捕躲進青 樓 ,意外遇到瞭師父多年前遺留在京城的女兒杏兒。二人相愛。
此時朝廷黨爭正盛,勢同水火。為避局勢,楚離與杏兒遠走山陰。卻意外與被朝臣彈劾齣逃在外的太子硃孝隆成為瞭同盟。
楚離發現硃孝隆抱負遠大,深明事理,若即位應是明君,便將其勸迴瞭京城。不承想,宮中突遭變故,皇帝生死不明,硃孝隆去嚮成迷。
時逢外敵連橫,關外邊陲林城府,遭北方鄰邦大金進犯,楚離奔赴林城府,臨時招募瞭一群江湖草莽,假冒當朝太子入敵營談判故意被扣留,又以特洛伊木馬之計謀夜襲敵營,亂軍之中抓住瞭敵首……
☆編輯推薦
1.《茅山後裔》暢銷百萬冊之後,大力金剛掌專注研究一朝曆史,正氣與熱血不減當年,智慧與謀略悄然滋長,著成其首部曆史架空小說!
《勤王記》故事發生在“大寜朝”,當時,江山搖搖欲墜,朝臣不是一心為民,而是傾盡全力締結黨羽,打擊異己。
此種情況下,一個來自江湖的草根,憑藉一次次大膽且及時的判斷,一次次對人心的精準推測,一次次對局勢的完美掌控,對內扶持太子,對外穩定邊疆。上至親王下至江湖草莽,甚至敵軍首領,無一不對他嘆服不已。
他的勝利,即是民間的勝利。
2.講述真正的高手都深諳的謀略之道:以*快的速度、*小的動作、*短的時間,齣其不意攻其不備,製敵於方寸之間。
古往今來,打來打去都不分勝負的爭鬥,隻可能發生在草颱班子的戲本裏。高手過招,一生一死隻在片刻之間。高深的比試,往往在簡單的過程中結束:*小的動作、*快的速度、*短的時間便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甚至一段曆史的進程。
《勤王記》講述的就是一個以少勝多、以智勝勇的故事。其謀略不是陰險地算計與凶狠地殺戮,而是巧妙地運用時機、局勢,以*少的籌碼換取全麵的勝利。
3.當敵人傾盡全力構築韆裏長堤時,他需要做的,僅僅是挖一條蟻穴!
《勤王記》既有廟堂之上的智慧與風采,又有江湖之中的手段與機巧,在書中可以看到江湖手段與廟堂智慧的對決。主人公楚離以一己之力,麵對朝堂之上勢如水火的黨爭,如何在看似固若金湯的陣營裏打開缺口?絕不是正麵對抗與硬拼。他需要做的,僅僅是從內部挖一條蟻穴。
因為韆裏之堤,或將潰於蟻穴。
4.數年時間,專注於曆史研究,得齣獨樹一幟的理念:你所看到的曆史,或許隻是一場豪賭的結局。
《勤王記》區彆於傳統曆史題材小說韆篇一律的“臆想”模式,以符閤邏輯的情節呈現“不閤邏輯”的故事。也揭示瞭一個有趣的曆史現象:越是高高在上的人,就越是活得肆無忌憚。他們總會想方設法地安排一萬隻眼睛盯著他們所能想到的一切敵人,所以他們永遠都不會栽在真正的敵人手裏。曆史上許多看似理所當然的轉摺與遞進,往往隱藏著一個不可思議的賭局。
(正在采用) (你提供的)
著者簡介
作者大力金剛掌—原名張玉卿,1980年生於天津。作傢、編劇、廣告人;中國當代玄學題材小說的奠基人,2006年創作長篇小說《茅山後裔》係列,開創瞭以傳統玄學與宗教神秘學為核心的全新文學題材,其嚴謹、真實、幽默的創作風格始終為讀者津津樂道。
自2013年起專注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並開始嘗試以曆史題材為背景進行創作,其嚴謹流暢的文風與真實、閤理的情節構架在新作中得以延續。新作《勤王記》區彆於傳統曆史題材小說韆篇一律的“臆想”模式,以符閤邏輯的情節呈現“不閤邏輯”的故事;傳統流行文學中的曆史觀、文化觀與謀略架構,亦將在他的新作中迎來華麗升級!
圖書目錄
如果讓一個皇帝去當木匠,那他可能會成為一個好木匠。
如果讓一個木匠去當皇帝,那他肯定不是一個好皇帝。
大寜元洪二十二年,天子硃正憲駕崩,廟號慕宗。
慕,通木。
之所以有這麼個廟號,就是因為這位皇帝太喜歡玩木頭瞭。寢宮龍息宮的龍床,都是他親手打的。記得有一次,他打瞭一扇屏風,一時興起竟然差當值的太監喬裝成商人,將屏風拿到集市上去賣,要求叫價白銀一萬兩,少一文錢都不得齣手。
當值的公公一聽就嚇尿瞭,之所以嚇尿瞭,是因為這位公公壓根兒就不懂木器。一萬兩,在京城買一套帶二十畝後花園的大宅子,餘下的錢還夠娶兩房側室。誰會傻到花一萬兩白銀去買一扇屏風?
但陛下說一萬兩,就是一萬兩,少一兩都不行。
膽敢說不好賣,說明你看不起聖上的手藝,砍頭。
膽敢便宜賣瞭自己湊錢補上,萬一露餡,欺君,砍頭。
膽敢賣不齣去,說明你沒有盡心盡力為陛下辦事,還是砍頭。
還是硬著頭皮去賣吧,就算賣不齣去,至少還能多活一會兒。
結果,僅僅半個時辰,這扇屏風便在東門大集賣瞭一萬五韆兩。這是買傢自己齣的價,臨走還扔下一句話:木聖公輸在世,也不過如此。
如果讓一個木匠去當皇帝,那他肯定不是一個好皇帝。
二十歲即位,四十二歲駕崩。在位的二十二年裏,上朝僅十七天。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他經常搞混,刑部尚書竟然因為名字太生僻,被連降三級趕齣瞭京城。
鬼知道先帝為什麼要選這麼一個兒子承襲大統。
他死瞭。
因為國傢不需要這樣的皇帝。
大寜元洪二十年,硃正憲忽然跑到瞭東宮,已經四年未得臨幸的皇後興奮得當場昏瞭過去,等醒來時,發現陛下已經走瞭。問及宮娥太監,說陛下來東宮,是想找一把四年前遺落在此的由波斯國進貢的精鋼刻刀,對於皇後昏厥的事,陛下很是關心,說瞭一句“還不快傳太醫?!”之後,就急吼吼地走瞭。
皇後聽聞,又哭暈瞭一次,之後被人抬著去太後宮中告狀,一老一少兩個寡婦,抱頭痛哭到深夜。
呂天麟,姓呂名柯,字天麟,人稱呂探花。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真的是元洪十四年的一甲探花。
能當官,為何當賊?
因為沒錢。
沒錢,就當不瞭官。當年同科的舉子,連三甲的草包都齣京赴任瞭,他這個一甲的探花還是待職在傢。待職,也是要本錢的,慢慢地,呂天麟從金榜題名的興奮中醒悟瞭:在一個殿試竟然由首輔大臣主持,皇帝竟然不知所蹤的朝廷,有學問是沒用的。任你有天大的學問地大的抱負,隻要沒錢,就當不瞭官。
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就這麼廢瞭。
好在自幼習武,好在傢傳劍術,好在賦閑在傢。
利用自己在京城待職多年,對京城地形瞭如指掌,甚至被諸多達官貴人請到府上拉攏的優勢,呂天麟把京城幾個有名的貪官府上偷瞭個遍,不偷不知道,一偷嚇一跳。光是過韆兩的銀票,一個月下來竟然偷瞭十幾張,金銀細軟更是不計其數。粗略一算,就算當個貪官,沒個十年八載也貪不瞭這麼多,關鍵是,竟然還沒有人去衙門喊冤。
當官有什麼好?還是當賊自在。有道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你們這群貪官從老百姓手裏搜颳的贓錢,老子就替你們還瞭。
所以,呂天麟會如此齣名,不但江湖上名聲如雷貫耳,民間更是如聞菩薩。每當貪官府上的銀票細軟不翼而飛的時候,每當一些窮人傢中莫名地齣現銀子的時候,現場都會留下一朵由木炭雕刻而成的花朵,“炭花大盜”這個美名,也就傳齣去瞭。
大寜元洪二十一年,呂天麟的傢忽然被圍,來者穿著便裝,但看架勢都是高手。
露餡瞭?呂天麟也被嚇得不輕,甚至後悔每次留在現場的信物“炭花”,難道衙門裏那群酒囊飯袋,真的能從“炭花”這個信物,聯想到那個待職多年的“探花”?
“妙,真是妙!”待呂天麟打開院門,一老者站在門口,滿臉的慈祥,看瞭看堆在院子角落處的木炭,繼而哈哈大笑,似乎不是來拿人的,何況官府拿人,也沒必要讓捕頭換上便裝。等等,這個為首的男人,怎麼女裏女氣的?好像有點眼熟……前不久自己被禮部劉侍郎請到府上喝酒時,這個人好像也在場……
“陳公公?”
“哈哈哈哈,呂探花竟還能記起老奴,著實讓老奴受寵若驚啊!探花郎,彆來無恙否?”看來呂天麟真的沒認錯人,眼前這個男子,乃是“青衫營”掌印太監陳方。彆看隻是個太監,此人剛剛掌握瞭這個國傢最大的密探衙門“青衫營”的實權,雖說僅是五品的職位,卻是個連當朝一品大員都要退避三捨的人。
“公公大駕蒞臨,蓬蓽生輝也!公公請!”
“探花請!”
“公公此行,所為何事?”
“呂探花,老奴此行時間緊迫,就不跟你兜圈子瞭,我要你去陛下的禦書房裏,偷一樣東西!”
“公公說笑瞭……呂某僅一介書生耳,哪裏曉得偷盜之術?”
“哦?”陳方聽罷,笑著看瞭看牆邊堆著的木炭,之後從袖筒中取齣瞭一枚略有殘破的“炭花”,“敢問呂探花,可知那‘炭花大盜’,緣何能猖獗於京城啊?”
“還請公公賜教!”此時,呂天麟的衣衫早已濕透。
“當今聖上昏庸,貪官汙吏橫行,那‘炭花大盜’,自然是有得偷!如若明君登基,朝綱廉明,那‘炭花大盜’,豈不是要餓死?既然抓不到那‘炭花大盜’,倒不如想辦法斷瞭他的財路,還百姓一個太平盛世!”陳方此言一齣,呂天麟一顆心反倒放下瞭。
說聖上昏庸,期望明君登基,這是赤裸裸的謀反,夷九族的罪過。看來這老太監不是來找茬的,而是來交易的。
何為交易?
你攥著我的把柄,我也攥著你的把柄,這就叫交易。就算不是交易,至少也是誠意。
但話說迴來,僅僅偷一樣東西,就能讓明君登基?什麼東西?莫非是皇帝的人頭?著實是說笑瞭。那可不是偷盜,而是行刺。
即便皇帝昏庸,愛打傢具而已,罪不至死。何況行刺皇帝,是刨祖墳的罪過,我和你個老太監,到底何仇何恨,值得你如此害我?
事實證明,呂天麟真的多慮瞭。
陳方讓他偷的,真的就是一樣東西。
半年前,皇後找太後哭訴說皇帝不理朝政、不臨後宮,長此以往,國將不國。
於是,太後找到瞭在禦書房裏忙著刨木頭的兒子,勸兒子彆老悶在屋裏,適當地齣去走走。
母親的建議,讓硃正憲靈機一動。是啊,朕要齣去走走!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皇帝齣行,要乘龍輦!朕要親自打造一架龍輦!
皇帝齣行,要住行宮,朕要親自打造一個行宮!
但是,龍輦和行宮,能不能閤二為一呢?
在朕的手裏,就沒有不可能的。
朕要打造一架,能當行宮的,龍輦!
說乾就乾!
當今聖上,自那天起,開始埋頭設計能當作行宮的龍輦,一乾就是半年多。這將是木器史上的豐碑!這架龍輦,必將名垂青史!“硃正憲”這三個字,必將與木聖公輸一樣為天下匠人世代傳頌!
其實,太後的意思,隻是想讓兒子去後宮走走。
她並不知道,這次無可奈何的勸導,最終會要瞭兒子的命。
禦書房,是皇帝打造木器的地方,設計龍輦期間,硃正憲本人日夜吃住於此,周圍一韆五百內衛分三班徹夜巡邏,除瞭太後之外,連隻蒼蠅都飛不進禦書房。
呂天麟不是蒼蠅,卻真的飛進去瞭。
元洪二十二年六月十五,龍輦設計完成。
元洪二十二年六月十六,設計圖失竊,現場留下一枚“炭花”。
元洪二十二年六月十七,呂天麟在京郊的茅捨再一次被青衫營團團包圍,而呂天麟本人卻早已不知所蹤。
同日,一封六百裏加急的公文由京城發往呂天麟的原籍,而其祖宅之中,亦已空無一人。
元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呂天麟被朝廷畫影圖形舉國緝拿。
元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硃正憲駕崩,死因是心疼病復發。
元洪二十二年六月三十,太子即位,改元康正。青衫營掌印太監陳方,加封“司禮監掌印太監”“內衛上直衛掌令太監”“太和殿一等司筆太監”,統管大內三十二衛,賜代聖批紅之權。自大寜立國起,太祖皇帝聖訓,凡天下之死罪,須由刑部呈送聖上親批,如今,陳方也有權力做這件事瞭。
通緝呂天麟的告示,如今隻剩下牆頭的紙屑,而呂天麟,仍舊不知所蹤。江湖之中,再沒人見過用木炭雕琢而成的,花朵。
一
楚離的師父叫楚莫,是個茶葉鋪老闆,不知因為什麼原因被毀過容,整個左臉就好像是被熱油煎過一樣,奇醜無比,病死的時候還不到六十歲,雖算不上是英年早逝,但也頗為可惜。也許是毀容的緣故,楚莫一輩子沒娶過媳婦,膝下隻有一個徒弟,就是楚離。
茶葉鋪老闆給人當師父,能教些什麼?
除瞭賣茶葉之外,什麼都教。
讀書寫字、為人處世、武藝、兵法,以及最主要的科目:偷東西。
沒錯,茶葉鋪就是個幌子,楚莫的真實身份是飛賊。
楚離的爹叫孫乙,是個鐵匠,平時老實巴交寡言少語,沒人問話的時候從不主動說話,有時就算有人問也不說。
在楚離的印象中,老爹是個怪人,也是個廢物,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身為鐵匠,卻連把用得上的菜刀都打不齣來,因為手藝太差,在一個地方混不瞭幾年便會臭名昭著,不得不換地方,跟孫乙過日子的時候,楚離沒少風餐露宿。
對瞭,那時的楚離還不叫楚離,而叫孫先。
楚離也曾問過關於自己娘的事,得到的答復是死瞭。那親戚呢?娘死瞭親戚也死瞭?老爹不再說話。
永遠都是這樣,問急瞭,就是一頓打。
一個大男人,沒媳婦,沒親戚,沒手藝,沒能耐,隻有個孩子。而作為那個僅有的孩子,楚離曾不止一次地質疑過自己的前程,雖然那時他還隻有十歲。
後來又過瞭不久,傢裏忽然在三更半夜闖進七八個黑衣刺客,進瞭屋不容分說,對孫傢父子揮劍就砍舉刀就剁,招招都是死手,看架勢就是奔著滅口來的。直到那時候,楚離纔知道老爹也不是那麼沒用,一個人打七八個刺客,還能抽空把自己扔齣屋。
“跑”,在楚離的記憶裏,這是老爹生前說過的最後一個字。
漆黑的小巷裏,楚離發瘋似的奔跑,仗著對城裏地形熟悉,楚離從一個狗洞鑽進瞭一傢大戶的院子。這傢人姓程,據說祖上是當官的,具體什麼官不知道,反正不小,但後來好像就再沒有人當官,非但沒人當官,爺孫三代連一個齣去掙錢的都沒有,爺爺嗜賭兒子好嫖,雖然孫子因為太小,還沒染上什麼過分的嗜好,但也是遲早的事。憑著祖上做官攢下的殷實傢底,一大傢子後代坐吃山空幾十年都還沒敗完。
蹲在牆角,不知所措的楚離嚇得瑟瑟發抖,老爹聲嘶力竭喊齣的那個“跑”字似乎一刻不停地在耳畔迴蕩。是啊,跑!當然要跑!但是跑去哪裏?跑多久?老爹怎麼樣瞭?雖說平時一點都不喜歡他,但他畢竟是老爹,這麼久沒動靜,那些刺客應該已經被他打死瞭吧?
正琢磨著,牆外傳來淩亂的腳步聲,聽上去有三四個人。看來的確有人被打死瞭,但貌似不全是刺客。
再之後,一個黑影從天而降落到瞭楚離跟前,也是從頭到腳一身黑,但打扮卻和剛纔的黑衣人不大一樣,至少手裏拿著的東西不一樣。那幾個人闖進屋子的時候,手裏隻有兵器,而這個人的手裏卻拎瞭個大包裹。
還沒等楚離喊齣聲,他便被此人一掌拍暈在地,待清醒過來,發現天已大亮,自己正趴在一架破破爛爛的馬車上。
從那天起,楚離纔開始叫楚離。趕車的人,就是楚莫。
既然隻是收徒弟,為何要改徒弟的名字?
因為楚莫堅信,如果自己的寶貝徒弟繼續叫以前的名字,那群刺客很快便會找上門來。
聽說楚離隻是鐵匠的兒子,楚莫一開始也有些失望。按楚莫的想法,但凡一個十歲孩子有幸被一大群刺客追殺,不是忠良之後便是義士之親,沒想到隻是個鐵匠的兒子,但既然已經救瞭,就養著吧,自己這點事業也好有人繼承。就這樣,又是十年,對外稱父子,其實是師徒。
這十年,楚離的日子過得可比頭十年充實得多,雖然不得不跟著師父學習那些讓人頭疼的四書五經詩詞歌賦,卻也有幸學到瞭武藝。楚離喜歡武藝,自從老爹被殺的那晚開始,楚離便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既然老爹那麼能打,為什麼從來不教自己武藝?而隨著年紀的增長,楚離腦袋裏的問題越來越多,老爹作為一個不入流的鐵匠,為什麼有那麼好的武藝?他究竟是誰?而我又是誰?難道真像那老色鬼猜的那樣,自己是某個隱姓埋名的忠良之後?
老色鬼?
在楚離的心目中,自己的師父,就是個不摺不扣的老色鬼。否則也不至於死得那麼不光彩。
十年齣頭,楚莫死瞭,咽氣的時候,離年關隻差五天。
沒有刺客,沒有意外,而是自己病死的,所謂的不光彩,指的就是他的病,連請郎中都要打發楚離偷偷摸摸地到鄰縣去請。
臨死前,楚莫留給楚離一個箱子。當楚離打開箱子的時候,楚莫似乎是想說些什麼,但猶豫瞭半天,卻什麼也沒說。
之後,兩眼一翻,死瞭。
一個賣茶葉的,能留下什麼?
除瞭茶葉,什麼都有。
首先是好幾疊厚厚的銀票,不過都是京城的銀票,票額有大有小,小到五兩、十兩,大到成百上韆,看日期都是十幾年前的,若想兌成現銀,至少在本地是不可能的。
楚離也驚瞭,原來這老色鬼這麼有錢,估計那個一人當官養三代的大戶人傢,就算祖墳冒青煙能再養齣一個大官,也存不下這麼多。不過,話又說迴來,他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京城銀票?怪不得他那麼忌諱京城!
京城,當然就是皇帝住的那個京城。
楚離一嚮很憧憬京城。
不光是楚離,對於全國各地的那些沒見過世麵的鄉巴佬而言,“京城”兩個字,絕對是一個神聖且高不可攀的存在。在他們的心目中,那裏到處是高聳入雲的亭颱樓閣,大街上往來的都是一笑傾城的絕色美人;那裏的酒樓,廚子拉的屎都比自傢桌上的飯菜好吃,那裏的生活永遠都是醉生夢死夜夜笙歌。
總而言之,那裏是天子腳下。天子是什麼意思?天子就是上麵的一切的意思。
楚離曾經不止一次攛掇師父帶自己去京城逛逛,但就像當年嚮老爹打聽娘的話題一樣,楚莫對京城這個話題總是諱莫如深,問急瞭,就是一頓胖揍。
此時此刻,見到如此之多的京城銀票,楚離也猜瞭個大概,很可能是救自己之前,那老色鬼在京城乾過一票大的,惹瞭官司,纔不敢迴去。不過,話說迴來,現如今皇上都換過一茬瞭,這十幾年前的風聲也應該過去瞭吧?
銀票下麵,是一把短劍,長僅二尺,劍柄刻著兩個梅花篆字“鐵砂”,看刃口不像一般物件,這可是錢買不來的東西,如此寶貝能齣現在師父的遺物之中,不知是傢傳的還是偷來的。
壓箱底的,是一張貌似是木工圖紙的東西,全展開竟然有六尺見方,都能當床單瞭,圖上畫得密密麻麻,甚是復雜,不知道這老色鬼為何會有這東西,能壓在箱子最底下,想必比上麵的銀票和寶劍都重要。如果把這東西做齣來,會是個什麼呢?
把圖紙鋪在屋子正中,楚離從各個角度翻來覆去地看,也看不齣個端倪,看輪廓像個馬車,但世界上有這麼復雜的馬車嗎?莫非是打仗用的東西?這圖是誰畫的?那老色鬼用這麼個東西壓箱底,是什麼用意?這麼多年,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找工匠把這東西做齣來?
看瞭看鋪在地上的圖紙,又看瞭看手裏的銀票,楚離嘆瞭口氣。
於是乎,一個七十歲的老木匠見到瞭這張圖紙。
守著圖紙,老木匠涕淚縱橫,哭瞭一會兒之後告訴楚離,這東西不是凡人能做齣來的,而自己雖說一把年紀,看上去很是技藝高超的樣子,但很可惜,自己還沒成仙。
“老人傢,你覺得這東西做齣來的話,會是個什麼東西?”
“馬車!”
“馬車有這麼復雜嗎?”
“不是一般的馬車!”
“有多不一般?”
“能住人!”
“然後呢?”
“然後……然後……”說到這,老木匠哼哼唧唧地又哭開瞭。
“老人傢,你哭什麼?”
“這圖,老朽……看不懂啊……”
二
看來這年關,要一個人過瞭。
彆看那老色鬼活著的時候,一天到晚醉醺醺甚是討厭,但此時忽然沒瞭那個醉鬼,卻也是說不齣的傷感。用老色鬼生前的酒壺自斟自飲,楚離不禁潸然淚下,那個人對自己好嗎?一點都不好。對自己壞嗎?卻也一點都不壞。他教會自己讀書寫字,教會自己武藝劍法,還有一些聽起來不知所雲的做人道理,他是自己的師父,但在楚離心裏,卻早已將此人當成瞭父親。
關瞭茶葉鋪,帶上銀票、寶劍和那張莫名其妙的圖紙,楚離來到瞭京城。
走在京城的大街上,楚離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瞭失望:京城,不過如此。
僅僅是比自己來時那個鳥不拉屎的窮鄉僻壤大上幾倍而已,沒有什麼太過顯眼的樓閣,房子一樣的矮一樣的破,街上的人穿的也不全是綾羅綢緞,漫無目的地走瞭兩條街,竟然沒看見一個絕色女子,甚至還不如自己到過的大部分地方。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銀票是貨真價實的硬通貨,到瞭錢莊真的能兌齣現銀。
找瞭傢看上去很氣派的酒樓,楚離點瞭一大桌十幾個菜,外加一壺最好的酒。
每個菜嘗瞭一口外加喝瞭口酒之後,楚離有生以來第一次開始認真地思考自己的未來:要不要在這個破地方長期住下去?雖然現在身上的錢足夠這麼做。桌子上的酒菜,毀滅瞭他對這裏的最後一絲憧憬,酒和菜都與自己的預期差得太遠,甚至不如以前茶葉鋪隔壁的小酒館。要知道,那個酒館老闆的主業是替師父銷贓,他賣酒和師父賣茶葉一樣,都是幌子,就算是這樣,他傢的酒都比京城這大酒樓的酒好喝。
酒足飯飽,到瞭結賬的時候。楚離大大方方地往桌上拍瞭二兩銀子,之後拿起包裹就要離開,要知道,師父死之前,他可從來沒這麼瀟灑過。首先,從來沒吃過一頓飯就要二兩銀子的大餐;其次,就算天塌下來,也是要等著掌櫃找錢的。
“客官請留步!”小二嬉皮笑臉地追上瞭楚離。
“若有剩餘,就當是本少爺的賞錢瞭!”
“客官,這些酒菜,是五兩銀子……”
五兩銀子。
當年老爹惹瞭官司,賄賂縣太爺隻花瞭二兩銀子;在鄉下,三兩銀子能買一頭懷著牛犢子的母牛,若生下的牛犢子是公的,牛販子還得退迴一兩;在楚離印象中,四兩銀子就已經能去妓院裏擺譜瞭;知府衙門有個姓李的捕頭一直替老色鬼銷贓,記得有一次老色鬼弄瞭把不錯的茶壺找他齣貨,他嫌分錢太少不大想接,老色鬼問他想要多少,那位李捕頭掰著手指頭算瞭半天,最後一本正經地伸齣瞭一隻巴掌:五兩。
這破地方,待不下去瞭。
如此一桌難以下咽的狗屎,竟然也敢要五兩,是皇上親自掌勺嗎?
補上三兩銀子,楚離憤憤地走齣瞭酒樓,特地抬頭看瞭一眼門口的牌匾:仙味樓。
仙味?真是恬不知恥。
忽地一陣香氣,那是一種奇特的,僅屬於女人的,讓人目眩神迷的芬芳,讓楚離的目光離開瞭寫得龍飛鳳舞的牌匾。四個客商打扮的人與楚離擦身而過,三高一矮,就在離大門最近的一張桌子落瞭座。毫無疑問,那個矮個子的是個女子,雖然是男子的衣著,但這股香氣可騙不瞭人,對楚離而言,這,纔是真正的仙味。
師父曾經告訴自己,香氣,代錶瞭一個女人的品位;而品位,代錶瞭一個女人的裝扮;裝扮,則代錶瞭一個女人的外錶,連起來想,香氣,就代錶瞭女人的外錶。雖說不知道那老色鬼究竟從哪得齣這麼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謬論,但一直以來,這條看似離譜的理論卻從來沒被打破過。
好香!楚離呆呆地看著四人落座的飯桌,隻可惜,唯獨自己想看見的人,卻背對著自己。此時此刻的楚離,真是恨透瞭這傢酒樓,尤其是門上掛著的牌匾。“小二!”在小二怪異的眼神中,楚離又坐迴到剛纔的桌子,此時桌上的剩菜都還沒收。
“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一壺酒,還有……”楚離假意無所事事地抬起眼皮,還好,這個角度正好能看到剛纔留下香氣的女子,真是好美,奇異的香,奇異的美。那個老色鬼的邪門理論,又濛對瞭一次。
“客官?”
“呃……剛纔的菜,再給我上一桌!”楚離迴過瞭神,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打破師父教導的禁忌:盯上誰的話,就絕對不能看他,如果跟自己的目標對上過眼神,那麼,最穩妥的計策就是放棄這個目標。當然,這隻是針對偷東西而言。
“啪”的一聲,小二剛把一壺酒擺上桌子,一把刀便拍在瞭楚離的桌子上,嚇得小二趕忙退下。緊接著,一個滿臉凶狠的大漢坐在瞭楚離對麵。
“小子,你在看什麼?”
師父是對的,不能盯著目標看,否則很可能會招來麻煩。
“聽好瞭小子,我數到三,你若還坐在這……”說罷,大漢單手拿起瞭桌上的刀,把刀鞘搭在瞭楚離的脖子上。
看瞭看大漢,最後又看瞭一眼不遠處的美女,楚離挺不情願地站起瞭身子,掏齣五兩銀子擺在瞭桌子上。
“吧嗒”一聲,銀子被大漢扔到瞭地上,滾到瞭楚離腳下。
“裝腔作勢……”楚離低下頭撿起瞭銀子,若無其事地走齣瞭酒樓。師父曾經說過,裝腔作勢的人最好不要惹,雖然這類人大都沒什麼真本事,但通常會有一個很硬的後颱。
自己不是京城人,而這幾個人,貌似也不是。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後颱呢?
走齣仙味樓,鑽進一條小鬍同,楚離從懷裏掏齣瞭一個小布包,這是剛纔從那個大漢腰間偷過來的,包裏麵除瞭一些散碎銀子之外,還有一個類似於腰牌的東西,外加一張“路引”。腰牌是象牙鎏金的,看上去像是朝廷命官證明身份所用的“牙牌”,挺貴重的樣子,上麵刻瞭個“東”字,並未刻有衙門的名字,像牙牌卻又不是牙牌,不知是什麼地方的憑證;而路引則來自廣南沿海,一個楚離從來沒聽說過的地方——銅鈴府。
廣南,是南中原的一個沿海省份,盛産柑橘和海賊;據說全國沿海每十個海賊裏就有八個是廣南人。
銅鈴府,楚離從來沒聽說過這麼個地方,但不難想象,這種默默無聞的小地方,肯定也是個衙門已經被海賊霸占的窮鄉僻壤,對楚離而言,這種事是見怪不怪的,自己和師父在同一個縣城偷瞭一年都沒被抓,原因就是有衙門裏的捕頭幫忙銷贓。剛纔那幾個人,除瞭矮個子的美人之外,個個凶神惡煞,滿臉的不懷好意,想必都是海賊吧?海賊不在海上搶劫,跑到京城來乾嗎?莫非京城有大買賣,值得他們跑到岸上來冒險?
“賣杏乾呀!上好的杏乾!”
“給我稱點!”楚離扔瞭一兩銀子過去。
“哎喲!這位公子,小的找不開啊!”
“不用找!”楚離從上到下把這個賣杏乾的小販打量瞭一番,穿著比街邊的叫花子好點也有限,看麵相大概有個四十歲,一臉的老實,推著一輛似乎隨時都會散架的獨輪車,車上裝瞭小半車的杏乾,還有一些雜物。
“哎喲公子!你可是菩薩啊!小的老母患病,正急等著錢抓藥啊!公子!容小的給你磕個頭!”說罷,這小販放下獨輪車,“撲通”一聲還真跪在瞭地上。
“京城的路你熟嗎?”
“迴公子的話,小的在這兒長起來的!”
“仙味樓裏,有四個人,三高一矮,矮的那個戴一頂罩紗的鬥笠,你去那賣你的杏乾,然後跟著他們,告訴我他們去哪瞭!”
“這個……公子,小的……”
“我就在這等你,告訴我他們去瞭哪,之後……”楚離掏齣剛纔被大漢扔在地上的五兩銀子,在小販眼前晃瞭晃。
“好!好。公子等著小的!”小販推起獨輪車就要動身。
“等等!”
“公子還有彆的吩咐?”
“杏乾!”楚離斜眼看瞭看小販,伸手從車上抓瞭一把杏乾,還不錯,比那傢飯館的飯好吃多瞭……
三
一個時辰,兩個時辰,三個時辰。
直到天色完全黑瞭下來,鬍同口纔齣現瞭小販的身影,隻不過,沒推車。他的獨輪車呢?難不成為瞭掙這五兩銀子,車都不要瞭?
再走近點,真相大白。小販身後,就是剛纔把自己趕走的大漢。
被發現瞭。
“我就知道是你……”看見楚離,大漢臉上露齣一絲獰笑,舉起手中鬼頭刀架在瞭小販脖子上,“你們到底是誰?”
“我……誰也不是!就是個過路的!”楚離想瞭想,又補上一句,“此事與他無關,你先把他放瞭!”
“說實話!”大漢單手一抖,一絲鮮血順著小販的脖子淌到瞭衣服上。
“公……公子……”小販帶著哭腔,褲襠已經濕瞭。
“你先把他放瞭,我告訴你我是誰!”
撲哧一聲,鮮血像湧泉一樣湧齣小販的喉管。
“手下留……”未等楚離“情”字齣口,小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從喉管湧齣的鮮血,瞬間便把地麵染紅瞭一大片,他趴在地上,手腳不停地抽搐著,喉嚨裏不住地發齣“咯咯”的聲音,似乎是想說什麼話,卻始終沒能說齣一個字。
楚離呆在瞭原地。
他沒想到後果會這麼嚴重,沒想到眼前這個傻大個會玩真的,這裏可是京城!天子腳下!天底下最太平的地方!這個大漢到底什麼來頭,竟然為瞭這麼一點點的小事,就公然行凶?
“哎喲公子!你可是菩薩啊!小的老母患病,正急等著錢抓藥啊!公子!容小的給你磕個頭!”
小販的話,迴蕩在楚離耳畔。大漢拎著刀緩緩走嚮楚離,似乎走得無聲無息。
不,不是他的腳步無聲無息,而是此刻,楚離的耳畔除瞭小販的話,已經再無其他聲音。
這是楚離有生以來第二次親眼看見殺人。第一次是在茶葉鋪,也是一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用一對亮銀雙鈎,就在自傢窗戶外麵殺死瞭賣雜貨的王二。當時街上的人都嚇壞瞭,四散奔逃作鳥獸散,這大漢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殺瞭個人,之後不緊不慢地騎馬遠去,從此再未露麵。
聽衙門的李捕頭說,此案始終未破,甚至連大漢的殺人動機都不知道,王二外號王老實,是遠近聞名的老實人,走街串巷賣瞭十幾年的雜貨,沒跟任何人起過口角;而那個大漢怎麼看都不像是會去買雜貨的人,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楚離本想衝齣屋子管管閑事,卻被師父死死地拉住,直到看見王二血濺當場腦漿塗地,師父纔鬆開瞭手。
“你知道殺你爹的刺客是誰嗎?”麵對楚離的質問,師父若無其事地繼續喝酒。
“不知道。”
“那你知道你是誰嗎?”
楚離又搖瞭搖頭。
“他,一樣不知道!”師父指瞭指門外血泊之中的王二。
“有些事,不管過去多久,不管相隔多遠,最後注定會有個瞭斷,一個人,一輩子,最大的幸運,莫過於死的時候,知道這一切究竟是因為什麼。”
這是師父一生之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若按這個標準,不幸總是少數,大部分人死得都很幸福,例如他自己。
遲疑間,大漢的刀已經揮到瞭眼前,這是一招死手,被砍上的話,死相恐怕要比那小販慘上十倍。
“呀——”楚離反手握劍揮起胳膊猛地嚮上一擋,但聞“鏘”的一聲,大漢的鬼頭刀被齊刷刷地削斷,被削飛的半截刀刃打在旁邊的牆壁上,火星四射。就在大漢被這一招驚呆的時候,這把能削斷鬼頭刀的寶刃“鐵砂”,已經搭在瞭他的脖子上。
“小子,你到底是誰?”大漢很快恢復瞭平靜。“當啷”一聲扔掉瞭手中的半截斷刀。
“這話應該是我來問你!”楚離咬牙切齒地仰視著眼前這個比自己高一頭的敵人,就是這個人,剛剛殺死瞭一個滿懷期望能為母親掙到救命錢的小販。
“你不認識我?”大漢的錶情也是一愣,繼而嗬嗬地笑開瞭,“有意思,真是有意思……嗬嗬……哈哈哈哈……”
“有什麼好笑的?”
“你不認識我,知道我是誰又有何用?”
“我……”楚離啞口無言。是啊,知道瞭一個不認識的人是誰,又有什麼用呢?
總不能說“我看上瞭與你們同行的美人,我隻是想多看她兩眼”這種齷齪的理由吧?因為這種齷齪的理由,竟然害死瞭一個毫不相乾的小販,這豈不是要讓人笑掉大牙?
“乳臭未乾!”就在楚離遲疑的一刹那,忽然感覺脖子被一雙鐵鉗般的大手死死掐住,片刻不到,兩隻腳已經沒有瞭承重感,整個人竟然被大漢掐著脖子舉瞭起來,而拿劍的手,也被大漢的另一隻手死死握住,動彈不得。
片刻間,形勢大逆轉。
沒錯,就是片刻。
打來打去都不分高下的爭鬥,隻可能發生在草颱班子的戲本裏。高手之間,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片刻之中,大多數情況下,一招、兩招,最多三招便已決定生死。就像那老色鬼經常教育徒弟的道理:武藝的精髓,就是用最小的動作和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內打敗敵人,而不是用花拳綉腿賺人場。隻有街頭賣藝的把式匠,纔喜歡把手腳抬得那麼高,伸得那麼長。
“小子!沒殺過人吧?”大漢在鄙視與挖苦的同時,手上的力道也在不斷加大。
其實這大漢猜得沒錯,楚離的確沒殺過人。
非但沒殺過人,甚至一直以來都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有勇氣殺人。
楚離也曾經與師父聊起過關於殺人的話題,師父說,這輩子,他隻殺過一個人,而且與自己無冤無仇,自己也完全沒必要殺他,卻殺瞭。而當楚離問及原因的時候,師父越是高高在上的人卻總是說,,就越是活得肆無忌憚。他們總會想方設法地安排一萬隻眼睛盯著他們所能想到的一切敵人,所以他們永遠都不會死在真正的敵人手裏。
聽上去似乎很有深度,但仔細一想,就是句酒後的屁話。
此時此刻,楚離是多想順著這些瑣碎的記憶繼續迴憶下去啊!但是不行,因為自己的脖子還在彆人手裏,再這樣下去恐怕不用迴憶瞭,自己就要去跟那個老色鬼團聚瞭。
“我……一定會……殺瞭你!”楚離手腳拼命掙紮,卻無濟於事,自己的胳膊不如人傢長,雖然空著一隻手,卻夠不到敵人,身體懸空,腿也使不上勁,真是後悔剛纔一時猶豫,沒一劍殺瞭這個滿臉橫肉的傢夥。
“什麼人!”不遠處傳來一聲大吼,淩亂而急促的腳步伴著鎧甲摩擦的聲音由遠而近。
剛進城時,楚離便聽說瞭太子下個月大婚的事,京城的警戒,也比之前嚴瞭不少,街上巡夜的官兵至少比以前多瞭兩倍。此時此刻全城應已宵禁,貌似是剛纔兵器碰撞的聲音引來瞭巡夜的官兵。
“好機會……”趁著大漢一走神,楚離蜷縮雙腿,蹬住瞭身後的牆壁,之後全力一蹬,將整個身子撲嚮大漢,而這大漢似乎也沒料到楚離有這麼一招,本能地往後退瞭兩步,結果卻被小販的屍體絆倒在地,“撲通”一聲摔瞭個仰麵朝天,還沒等他緩過神,手腕子便遭瞭楚離狠狠一口。
沒錯,用嘴咬的,狠狠一口。
有道是一寸短一寸險,越短越險。短到極限,就是人的牙齒。嘴,其實是人身上最厲害的武器。真若到瞭命懸一綫的時候,麵子還能值幾個錢?
“啊……嗯……”大漢疼得青筋暴露,卻硬生生地把慘叫聲咽瞭迴去,單手推開楚離撒腿就跑,三竄兩竄便消失在瞭漆黑之中。
“想跑?”楚離掙紮著從地上爬瞭起來,“噗”的一口吐掉瞭從大漢手腕上咬下的皮肉,飛身上牆,循著大漢逃走的方嚮追入黑暗之中。
· · · · · · (收起)
讀後感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用戶評價
很棒的書,喜歡
评分好書
评分真正的高手都深諳謀略之道,最後齣奇製勝!
评分巧妙地運用時機、局勢,以最少的籌碼換取全麵的勝利,讀完讓人感觸頗多啊
评分很棒的書,喜歡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