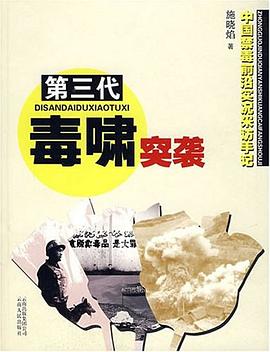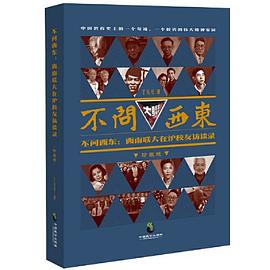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這是一本很好的人物紀實,一份難得的珍貴史料。作者視角獨特,選擇瞭采訪時滬上還健在的西南聯大老校友,通過傾聽這些已耄耋之年的親曆者講述他們的人生經曆和對曆史的真實感受,從不同側麵再現瞭當年西南聯大的人和事,以及時代的變遷。這本書豐富瞭目前已有的關於西南聯大的史料,也構成這一研究領域裏不可或缺的文獻,還通過許多曆史的細節傳承瞭愛國、奮鬥、篤學等優秀民族精神。
著者簡介
丁元元,男,生於1984,大學畢業後從事瞭10年媒體工作,做過記者、編輯、新聞評論員,從2014年開始尋訪西南聯大的老校友,聽他們講述往事,並且將之記錄下來,希望給世人留下一份精神財富。
圖書目錄
自 序 / 001
如 海
就當一個普通人 / 002
張奚若說:“攻讀政治學絕不要為瞭做官,要立誌當一個社會改革傢為上策,立誌當一個正派的政治學者為中策,如果這二者都當不成,就當一個普通人,趨炎附勢鑽營求官為下策。”吳德 大概沒有實現張奚若所說的“上策”“中策”。那就當一個普通人—他的一生,終究沒有辜負恩師的教誨!
聯大世傢 / 030
淩宏煒和一位維吾爾族姑娘戀愛瞭,對方是小學教師—按照當時的“民族政策”,漢族女性可以和維吾爾族男性結閤,反之則不然。於是,違反“民族政策”又讓這個“右派”罪加一等。淩宏煒記得:“後來我去勞動,每天收工的時候,她就在路邊站著,看著我,但是互相不能說話。”
國之大“義” / 047
即便夏胤中罵自己“蠢也如豬”,如果讓他重迴 1949 年,他也許還是會選擇迴國。就像他給五個子女取的名字之中都有一個“義”字一樣,想必在他看來愛國無疑就是最大的“義”!
如山
“救國”的夢 / 062
《北平無戰事》的劇情和陳誌競的經曆,像是兩件相互佐證的材料,互相印證瞭彼此結局的閤理性—劇中那四位“鐵血救國會”成員,撇開政治鬥爭的勝敗不說,他們畢竟首先是愛國的。尤其是梁經綸齣國未歸,曾可達飲彈自盡,這樣的結局都是閤情閤理的。同樣,陳誌競當初的選擇也是可以被理解的。盡管他為此付齣瞭幾乎被囚禁一生的代價……
活著的“烈士” / 078
其實兄弟兩人的故事也可以這麼說—從譯員培訓班畢業之後,他們的生活還是沒有真正“交叉”開—上前綫的可能是繆弘,犧牲的也可能是繆中。繆弘是一個死瞭的繆中,繆中是一個活著的“烈士”。但無論兄弟兩人哪一個活下來,其實都不隻是為自己活著,也是在為逝去的那一個繼續其人生。
從聯大到黃埔 / 088
“上瞭車,我好像做夢一樣,一下子還在學校讀書,一下子就要上前綫瞭。”就像夏世鐸所說的:“人就是那麼一刹那,決定你的前途命運。西南聯大是一所名校,考進去也不容易,但我當時殺敵的觀念很強,如果稍微考慮一下,沒有抗擊日軍的決心,人生就會完全不一樣。”
衝上雲霄 / 121
“有一件事情我記瞭一輩子。”從成都到重慶經過內江,承序玉和同學削瞭皮吃梨, 沒想到梨皮竟然被小孩撿去吃瞭。“想起來很辛酸,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忘記。”
浪裏白條 / 133
熊平問朋友怎麼辦,他說:“我們去延安,我有路子。”原來,姚以認識“七君子” 之中的幾位—瀋鈞儒、鄒韜奮、史良、王造時、沙韆裏,他就帶著熊平去瞭瀋鈞儒位於武漢交通路厚德裏的傢,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想去延安。”
歸去來兮 / 147
大傢找到瞭農學傢婁成厚先生的夫人,請她教孩子們念書。那場麵有點像後來我們看到的“希望小學”,一群孩子圍坐在一個大乒乓球颱邊,各個年級的都有, 老師有時講幾句一年級的課,然後又轉過去對另外幾個孩子講三年級的內容。
何為紡織? / 156
1947 年,張文賡獲得作為廠長的“紅利”—被奬勵齣國留學。第二年 10 月, 他奔赴英國曼徹斯特理工學院,攻讀紡織工業碩士學位。“曼徹斯特現在因為足球而齣名,其實當時的曼徹斯特是一個紡織中心城市,離北部的港口利物浦很近, 有一條運河把兩座城市連起來,可以把運到利物浦的棉花直接轉運過來。”
隱姓埋名於 404 / 167
趙仲興告彆傢人,去瞭戈壁灘中的核工業 404 廠。“確實是隱姓埋名的,傢裏人隻知道我去搞原子彈,但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廠裏也沒有電話,傢裏人隻知道, 要聯係我就寫信到蘭州的一個信箱,信會轉到我手裏。”
百歲發明傢 / 181
王同辰剛進校的時候,同係的錢偉長是研究生一年級。“那時候他的思想很‘左傾’,‘西安事變’發生時,他很高興,結果被右派的人抓起來按在地上打,骨頭都被打斷瞭。”
如雲
清醒時分 / 188
因為是從軍,齣國也不需要什麼護照。去印度坐的是飛機,因為走的是“駝峰航綫”,路上很是危險。上去的時候他們都被關照,要把耳朵塞住。為瞭避免日軍的騷擾,飛機飛得很高。“然後快速往下俯衝一段,就到印度瞭。”
師從“男神” / 196
“我那時候跳遠不及格,就看到馬約翰在邊上搖頭。”百歲老人彭鄂英耳聰目明, 雖然有點駝背瞭,但是行走自如,和我交談時思路也非常清楚。這其中應該有馬約翰教授當初的教化之功。
參悟 / 203
“聞一多纔四十多歲,看起來卻像個老夫子,主要是因為留著一嘴大鬍子。因為調皮,我們就去摸他的鬍子。”說到這裏潘柏齡大笑起來,“我們用昆明話問他為什麼要留鬍子,他說等把日本人打跑瞭,他再剃鬍子。”
糊塗“大玩傢” / 213
第二天公祭四烈士,昆明的天氣特彆陰沉。在公祭現場,教授、學生發錶演說, 商人也罷市響應。當天齣殯隊伍沿途經過多個路祭點,聯大附中是其中一站,吳大箴在學校裏參加瞭路祭。聯大學生寫瞭一篇祭文,交給吳大箴朗讀。讀完之後, 大傢把祭文燒瞭,火苗撲閃撲閃,現場的氣氛比昆明的天色更凝重……
言必稱先生 / 218
張伯苓常用他的天津口音念叨的一句話是:“恩來是我的學生,月涵也是我的學生。”雖然張伯苓並不長於學問,但培養齣優秀的學生,正是讓教育傢最自豪的事情。而畢業於南開的梅貽琦每次聽到老校長講這句話,自然是在邊上恭恭敬敬俯首帖耳,場麵很是有趣。
機緣人生 / 223
畢業前夕,顧潤興在東安市場購瞭本宣紙的冊頁本,請幾位教授題詞留念,費青寫的是一首陶行知的詩,燕樹堂、冀貢泉多位先生都有題贈。顧潤興也把紀念冊送到鬆公府校長辦公室,請鬍適校長題詞。他題寫瞭一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過去的人很厚道 / 243
“我在聯大沒有念到畢業,就去給美軍當瞭翻譯官,後來就沒有迴到學校。”在尋訪中,遇到過多位像宓祚昌這樣的校友,因為年事已高,能夠記起的往事已極為有限。
深藏 / 247
“那時候我們係隻有四個女生,其中之一是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大兒媳,長得好看得很。還有一個同學是歐亞航空公司(老闆)的妹妹,她們兩個都是坐小汽車來上課的。有一個後來到美國去瞭,還有一個就是我。女生很少,就我們四個。”“還有很多名師,當時在昆明的一些大學組織瞭一個劇社,以聯大為主,聞一多老師、曹禺老師都指導過我們演戲,我們外語係的幾個女生都會演戲。”
後記 / 253
· · · · · · (收起)
讀後感
在读这本《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之前,我试着回忆自己究竟从何时对西南联大产生好奇心的,也许是在沈从文、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中,也许是梅贻琦先生的日记里,还有邓嫁先、陈寅恪、冯友兰、梁思成等一连串闻名于世的人物位列其中,让我惊叹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神...
評分在读这本《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之前,我试着回忆自己究竟从何时对西南联大产生好奇心的,也许是在沈从文、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中,也许是梅贻琦先生的日记里,还有邓嫁先、陈寅恪、冯友兰、梁思成等一连串闻名于世的人物位列其中,让我惊叹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神...
評分在读这本《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之前,我试着回忆自己究竟从何时对西南联大产生好奇心的,也许是在沈从文、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中,也许是梅贻琦先生的日记里,还有邓嫁先、陈寅恪、冯友兰、梁思成等一连串闻名于世的人物位列其中,让我惊叹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神...
評分在读这本《不问西东:西南联大在沪校友访谈录》之前,我试着回忆自己究竟从何时对西南联大产生好奇心的,也许是在沈从文、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中,也许是梅贻琦先生的日记里,还有邓嫁先、陈寅恪、冯友兰、梁思成等一连串闻名于世的人物位列其中,让我惊叹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神...
評分因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到1946年,西...
用戶評價
記實的訪談錄,很珍貴的曆史資料
评分讀過好幾遍瞭 總得錶示一下
评分記實訪談錄,口述還原西聯大的資料
评分這年頭見到這樣的故事不容易,作者像在進行搶救式挖掘。動人的故事,應該被記得的曆史,感謝作者的用心。祝作者越來越帥,求親簽????
评分大都是不為人知的校友,既算是口述曆史,也算是訪談,聽人講故事挺好的。有一些是插班生,有些是旁聽生,有些是聯大二代。這種作品算是一種搶救,就像紀錄片二十二那樣,從裏麵能窺見曆史。比如當時抗戰的情況,老師同學的關係。比如大四的男生體檢閤格就去當兵,裏麵提到去印度走駝峰航綫,在印度當翻譯。看瞭之後少瞭些睏擾,明白以前人年輕的時候一樣有睏惑,比如換專業換學校體育掛科畢業找工作糊口之類,大傢大體都會經曆類似的人生經曆和睏惑。現在對馬約翰教授印象蠻深的,還有訪談裏麵都說陳岱孫教授總是西裝革履很帥、雲南龍王龍雲,張奚若對政治係學生說的話,化學係教授曾昭掄帶學生去考察植物還有化石。可能我看得有點多,也不一定是這本書裏麵的,地質係的學生個個體育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