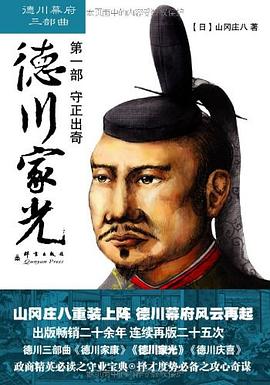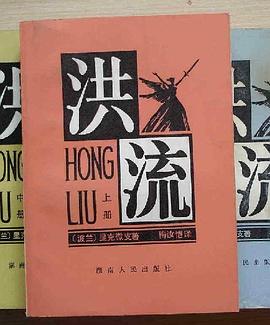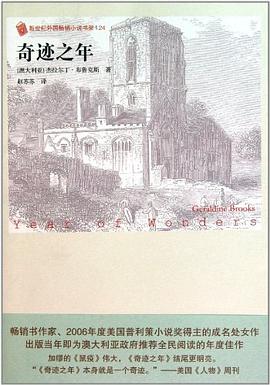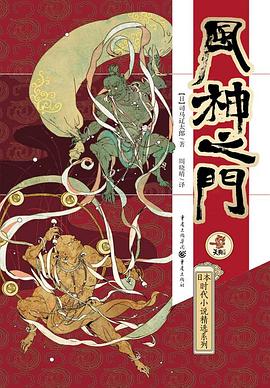具体描述
瀚海从来不怜惜弱者。一代又一代的征服者被它的铁手套教养成象苍狼一样勇敢、狡黠、能忍无穷痛苦、具备无限耐心的种族。如果他们没有成为征服者,就只有无名的白骨才会记得他们的历史。
狼族大汗也速该为宿敌塔塔尔人所杀,汗位被部将伊鲁克所篡,遗孀与子女被族人所弃,面对蒙古草原的酷烈寒冬自生自灭。
冬季来临,食物匮乏,一家人面临生存危机。铁木真手刃自私自利隐瞒食物的哥哥别克帖儿,无法接受真相的珂额伦一度将铁木真驱逐出去……面对四周强敌环伺、仇敌追杀,铁木真勇敢地存活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为替父报仇,重振家声,他收服了各部族人的心,成为了真正的成吉思汗。
作者简介
康恩·伊古尔登(Conn Iggulden),生于1971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著有「帝王系列」(Emperor Series)与「征服者系列」(Conqueror Series)等多部历史小说。2008年与弟弟哈尔合著的非文学畅销书《男孩的冒险书》亦获得广大反响,并已陆续推出一系列相关著作。
目录信息
苍茫大雪中,蒙古弓箭手团团围住塔塔儿人的劫掠部队。战士脚踩马镫,双膝驭马。一箭接一箭射出,却渐失准头。空气中弥漫着肃杀的沉默,无人出声。急促的马蹄声盖过伤者的喘息与寒风呼号。塔塔儿人寡不敌众,眼见逃不过战争黑翼下的死神召唤。马儿哀鸣,瘫倒在地,鼻腔喷出鲜血。
也速该站在土黄色岩石上观看这场战役,佝偻的身体紧裹在兽皮中。旷野上刺骨寒风不断呼啸,撕裂他失去羊脂保护的皮肤。也速该不动声色,多年来的艰困生活,已让他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痛觉。这是人生的一部分,就跟号令战士出动,要他们杀敌一样,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也速该鄙视塔塔儿人,但他们的确是勇猛的部族。也速该看着慌乱而逃的塔塔儿人拥向一个年轻战士周围,他穿着令也速该欣羡的锁子甲。那年轻人在风中简洁地发号施令,原本溃散的塔塔儿人立时停下脚步,也速该知道该是自己出动的时候了。他身旁的九个勇士也感受到这份心思。这九人是也速该部里最出色的战士,他们是立下血盟的兄弟与奴隶,凭着彪炳战功赢得身上雕着一只飞跃小狼的珍贵牛皮铠甲。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他说着,察觉到大家向他靠拢。
其中一匹母马兴奋嘶鸣,他的头号战将伊鲁克低声笑着。“小美人,我们会为你杀了他们。”伊鲁克边说边搓揉它的双耳。
也速该脚跟往马腹一蹬,所有勇士一齐出发,奔向正在厮杀呐喊的雪中战场。他们居高临下,可清楚看见狂风的行径。长生天伸出手,用夹带大量冰雪的白色长巾鞭笞摇摇欲坠的战士,也速该敬畏地发出低语。
也速该一行快速奔向战场,一路上队形不曾改变。多年来,这九人一直追随也速该,他们不用思考就可维持固定距离前进。他们要思考的只有待会怎样将敌人砍下马,让他们冰冷地倒在旷野中。
也速该的勇士冲进正在厮杀的战阵中央,杀向敌人刚冒出的领袖。他们知道如果让那人活命,就会留下祸根。也速该的坐骑径直冲向头号敌人,他笑了:今天还轮不到你。
这一冲,前方一个塔塔儿人来不及转身迎向新敌人便撞断脊梁,当场毙命。也速该一手抓着战马鬃毛,一手持刀,一刀一个,敌人如落叶纷纷倒地。两人攻向也速该,他若光靠手中这把父亲的长刀,可能会抵挡不住,于是便用坐骑冲撞敌人,再用刀柄猛力击倒一个无名士兵,杀进重围,直接攻向集结在战阵中央负隅顽抗的塔塔儿人。也速该的九名勇士紧跟在后,保护着自出生起就发誓追随的大汗。也速该不用看就知他们在后方保护自己,从塔塔儿首领打量他的眼神就能感觉到。对方或许也看到遍地僵直如箭的尸体。突袭攻势已被彻底击溃。
塔塔儿首领站在马镫上,挥着血红长刀扑来,也速该顿时血脉贲张。那人眼中全无惧色,只有因毫无斩获而起的愤怒与失望。风雪中的牺牲者带来的教训显然不够,但也速该知道塔塔儿部绝不会不知这场战役的惨烈。春天到来后,他们会发现已黑的尸骨,也就知道他的牲口是夺不得的。
也速该轻笑几声,这塔塔儿战士与他对望时皱起眉头。他们还是学不会啊,只靠妈妈的奶水可是会饿死的。他们很快又会再来,然后他会再次开战,让更多卑贱的人葬送刀下,这正中他的下怀。
他发现前来挑战的塔塔儿人是个小伙子。也速该想起东方山陵上即将诞生的孩子,有朝一日,不知他会不会也遇上一个与他持刀相对的华发战士。
“你叫什么名字?”也速该问道。
周遭的战斗已经结束,他率领的蒙古人开始在尸体间翻找有用的战利品。狂风仍在怒号,对方听到他的问题,也速该看见这年轻敌人对他皱眉。
“那你叫啥,牛鞭吗?”
也速该再次轻笑出声,但露在空气中的皮肤已微感刺痛,他有些累了。他们连续追踪这支劫掠部队两天,不眠不休跟着横越自己的领地,每天仅靠一丁点干奶块充饥。他的刀已准备再夺一命,他举起刀说:“小子,那不重要。上吧。”
这塔塔儿战士看到他那比箭更锐利的眼神,认命地点点头说:“我叫铁木真·兀格,来自一个伟大家族。我要是死了,一定会有人来报仇。”
他脚跟一蹬,驾着坐骑冲向也速该。大汗的刀破空挥出,一招即中,对方坠落在他脚下,马儿穿越战场狂奔而去。
“小子,现在你只是块腐肉。”也速该说,“就跟其他偷我牲口的人一样。”
他环顾四周,有四十七个离开毡帐随他出征的战士,与塔塔儿人的激战中,他们失去四位弟兄,这二十个塔塔儿人则无一生还。虽然付出极大代价,不过严冬逼得人不得不走上绝路。
“快搜。”也速该下令,“天色已晚,赶不及回去,我们就着岩石扎营。”
值钱的金属或弓是可交易的好货,或可拿来替换残破的武器。但除了锁子甲外,战利品并不多,这证明了也速该的推测,这群年轻战士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而出来试试身手,并没有誓死奋战的决心。他接过沾血铠甲挂上鞍角。他心想,做工实在精良,至少能挡住匕首刺击,这年轻战士有如此贵重之物,来头应该不小。于是那名字再次浮现心头。他耸耸肩。现在这不重要,他会把分得的马拿去和其他部落换些烈酒和毛皮。现在除了寒风有些刺骨,其实天气还算不错。
隔天早上,也速该一行人打道回营,暴风雪仍未减弱。只有外围的人策马迈着轻快步伐提防突袭。其他人紧裹皮袍,扛着战利品,脚步沉重,身躯半僵,浑身布满污雪与羊脂。
族人选的落脚处很好,倚着一片巉岩小丘,上头覆着在朔风中枯萎的苍苔,毡帐近乎完全隐没雪中。唯一的灯火是朦胧蒸气后的一丝微光,放哨警戒的眼尖男孩早就看到归营战士。听到告知归营的鸣笛声,也速该精神为之一振。
部落中的妇孺可能还没被笛声唤醒。在这酷寒之日,他们只会从睡梦中起来点火炉,大概要等用毛毡与柳条搭的大帐上覆冰融化半个到一个时辰后才会真正起身。
当马群趋近毡帐,也速该听到一声尖叫如灰烟窜出诃额伦的帐中,期盼之心不禁加速跳动。他已有个小男娃,但死神经常眷顾幼囝。只要营帐容得下,大汗的子嗣是越多越好。他低声祈祷,希望再生个男孩,替原本的儿子添个弟弟。
当他跃下马鞍,听见猎鹰在帐中尖啸,他每走一步,身上的皮甲就咯吱作响。他把缰绳交给披着皮袍呆立在旁的仆役,看都没看一眼就推开木门直奔帐中,盔上的积雪立刻融成一摊水。
“啊!下来!”他边说边笑,看着热情扑上身的两只猎犬,它们不停又亲又舔,绕着自己打转。他的猎鹰也叫了一声以示欢迎,但在他听来更像是期盼出门狩猎的心声。他的大儿子别克帖儿光着身子缩在一角,玩着坚硬如石的干奶块。也速该的目光一刻也未离开躺在毛皮上的女人。诃额伦因暖炉的热气而满脸通红,金黄灯光下,她的双眸十分明亮。她坚强而细致的脸上汗珠晶莹,他看见她的前额有一丝用手背抹汗留下的血痕。产婆正忙着处理一堆布。他从诃额伦的笑容得知自己又添了个儿子。
“给我看看。”也速该跨出一步。
产婆面有愠色,退后一步,满是皱纹的嘴嗫嚅着:“你的大手会弄疼孩子,让他先喝娘的奶,等长得壮点再抱吧。”
产婆把孩子放下,用布条擦拭孩子的手脚,也速该忍不住看了一眼。他身着皮袍俯视着母子俩。孩子似乎也看见他,立时号啕大哭。
“他知道是我。”也速该骄傲地说。
产婆不以为然地咕哝:“他还这么小。”
也速该没说话,俯首对着双颊红润的婴儿微笑,下一瞬间却脸色大变,立刻擒住产婆的双手。
“他手上是什么东西?”他厉声责问。
产婆正准备替婴儿擦手,但在也速该凌厉的目光下,她轻轻摊开婴儿的手掌,掌中有个眼球大小的血块随着脉搏微颤,闪着黑亮的油光。此时诃额伦起身察看孩子为何引起他的注意。看到那黑色团块时,她发出悲叹。
“他的右手握着血块。”她低语,“这一辈子都要出生入死。”
也速该倒抽一口气,希望她刚才没说那句话。他们真是大意,竟为这孩子招来厄运。他面带愁容,沉思片刻。产婆继续紧张地清理男婴,血块在毛皮上颤动。也速该伸手掬起血块,那东西在手中闪闪发亮。
“诃额伦,他生来就把死亡握在右手上,这再恰当不过。他是大汗之子,死亡是他的伙伴。他会是个优秀的战士。”他看着男婴最后被交到疲惫的母亲手中,凑近乳头就一阵狂吮。他母亲面孔微颤,然后紧闭双唇。
也速该转身面向产婆,语调依旧带着烦忧。
“老嬷嬷,做个骨占吧。且让我们看看这血块对狼族是好是坏。”他眼神黯淡,不用多说,这孩子的一生就看这骨占的结果。他是大汗,整个部落都盼他能让部族日益壮大。他相信自己的言语能让孩子免遭长生天之妒,却又害怕诃额伦一语成谶。
产婆低着头,知道接生仪式中必定招来某些可怖的东西。她伸手去拿炉边的一袋羊踝骨,上面是部落的孩子着上的红绿两色。根据骨头落地的不同形式,可分为马式、母牛式、绵羊式和牦牛式等等,还可用这些骨头玩上千种游戏。但耆老知道,若在适当时机与地点掷骨,就能得知更多信息。产婆抬手准备向后掷骨,却被也速该挡下。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她大吃一惊。
“他是我的骨肉,是我的小战士。让我来。”他从她手中接过四根羊骨。她无法抗拒,他的冷酷表情让她不寒而栗,连犬只与猎鹰也都静止不动。
也速该掷出羊骨,四支骨头完全停止后,产婆倒抽一口气。
“啊,四马是极度祥瑞之兆。他会是个马上健将,会在马上征服四方。”
也速该猛点头。他想让族人看看自己的儿子,要不是因为伺机往暖帐里钻的猛烈风雪,他真会这么做。酷寒是部落之敌,但也让部落日益强大。在苦寒中,年长者撑不了太久,孱弱的稚子也容易夭折。但他的孩子绝对不会如此。
也速该看着一丁点大的孩子抓着母亲柔软的乳房。孩子和自己一样有着狼眼般浅黄色的金色双瞳。诃额伦抬头向孩子的父亲点点头,他的骄傲让她大为释怀。她确信血块是不祥之兆,但骨卦让她放心不少。
产婆问诃额伦:“你帮他取名了吗?”
也速该立刻脱口回答。“我的儿子要叫铁木真。”他说:“他会像铁一样。”帐外,风雪继续呼号,毫无暂歇迹象。
· · · · · · (收起)
读后感
怎么说成吉思汗也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一个英国历史小说家,要通过五本小说来讲述这个英雄人物,实话实说,在没阅读之前,确实让我对这部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不过,当我读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曲解了这个英国人,这部英雄史诗原来在他笔下,依然可以...
评分怎么说成吉思汗也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一个英国历史小说家,要通过五本小说来讲述这个英雄人物,实话实说,在没阅读之前,确实让我对这部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不过,当我读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曲解了这个英国人,这部英雄史诗原来在他笔下,依然可以...
评分怎么说成吉思汗也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一个英国历史小说家,要通过五本小说来讲述这个英雄人物,实话实说,在没阅读之前,确实让我对这部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不过,当我读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曲解了这个英国人,这部英雄史诗原来在他笔下,依然可以...
评分怎么说成吉思汗也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一个英国历史小说家,要通过五本小说来讲述这个英雄人物,实话实说,在没阅读之前,确实让我对这部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不过,当我读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曲解了这个英国人,这部英雄史诗原来在他笔下,依然可以...
评分怎么说成吉思汗也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一个英国历史小说家,要通过五本小说来讲述这个英雄人物,实话实说,在没阅读之前,确实让我对这部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不过,当我读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后,我才知道我确实曲解了这个英国人,这部英雄史诗原来在他笔下,依然可以...
用户评价
与其说这是一本历史传记,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权力运作的教科书,只不过它的案例取材于遥远的过去。作者在阐述其军事策略时,展现了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分析能力,将地理、后勤、以及对手的文化弱点,拆解成可以被精确计算的变量。读到这些部分,我仿佛置身于一份最高级别的参谋报告中,所有的浪漫主义色彩都被剥离,剩下的只有对效率和胜利的极致追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不同文化体系冲突与融合的探讨。它没有采取简单的“文明冲突”的二元对立视角,而是揭示了在扩张与征服的过程中,新旧秩序如何交织、碰撞、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治理模式。这种多维度的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对“成功”和“失败”定义的理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往往碾碎的不仅仅是生命,更是固有的思维框架。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初读时略感疏离,但很快就被其独特的韵律所吸引。它不像某些严肃的历史著作那样枯燥乏味,反而带有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咏叹调,尤其是对自然环境的描绘,简直是神来之笔。那些广袤无垠的草原、严酷的冬季风暴,仿佛成了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要角色,它们塑造了人物的性格,也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这种将自然力量与人类意志抗衡的描写,赋予了整个故事一种悲壮的美感。我常常在阅读那些描述长途跋涉的章节时,能真切地感受到风沙扑面和水草丰美的对比,这种强烈的画面感,是很多依赖纯粹文字描述的作品难以企及的。它成功地将读者的感官体验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让“阅读”更像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评分这部作品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出色,作者似乎深谙如何在高潮迭起和沉静内省之间切换,让读者在磅礴的历史画卷中感受到人物的脉搏。我尤其欣赏那种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英雄事迹的罗列上,而是深入到决策者面对巨大压力时的挣扎与权衡。那种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对个体情感的捕捉,使得那些远古的战役和政治博弈不再是冰冷的史实,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复杂性。比如,书中对某次关键会议的场景描写,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每个人发言时的微表情和潜台词,都被勾勒得淋漓尽致。这种精雕细琢的笔法,让我在阅读时常常需要放慢速度,细细品味每一个转折点背后隐藏的深意。它不是那种一目十然的爽文,而是需要读者投入心神去解码的文本,每一次解读都有新的发现,这种智力上的参与感,是阅读体验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
评分从文学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章节安排堪称精妙的迷宫设计。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多线索叙事,时而跳跃到后方稳定统治的视角,时而聚焦于前线士兵的微小视角,这种视角的频繁切换,避免了单一主视角带来的单调性,使得整个故事的肌理异常丰富。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关键转折点设置的“留白”,它不是信息缺失,而是一种有意的引导,促使读者去填补那些未言明的恐惧、野心或遗憾。这种手法要求读者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因为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都可能成为理解后续情节走向的钥匙。对于那些习惯了被动接受信息的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但对于追求深度阅读体验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仿佛在参与作者共同构建一个宏大的世界。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对“合法性”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化处理。在书中,权力并非仅仅依靠武力来维持,更多的是依靠一种被构建出来的、具有神圣色彩的叙事体系。作者极其细致地描绘了这种叙事是如何通过宗教、盟约、以及精心设计的仪式,从一个游牧部落的领袖,逐步转变为被上天赋予使命的统治者的过程。这种从草莽到帝王的“身份升级”,远比单纯的军事胜利复杂得多。它探讨了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建立起一套能够被不同族群共同接受的道德和法律基础,这对于理解任何形式的长期统治都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读完之后,我不再仅仅关注他“打赢了多少仗”,而是思考他“如何赢得了人心和信仰的持久支持”。
评分很有气势的书
评分热血沸腾!可惜成吉思汗死后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评分很有气势的书
评分热血沸腾!可惜成吉思汗死后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评分弑兄者铁木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