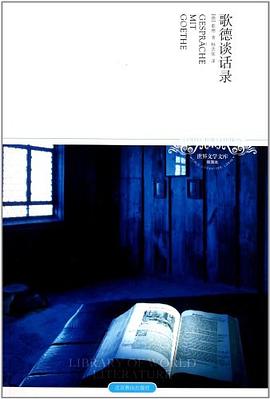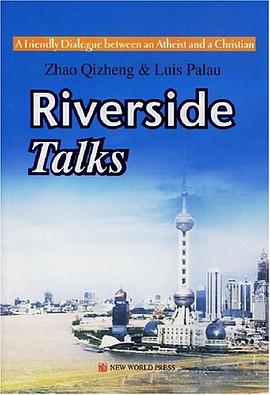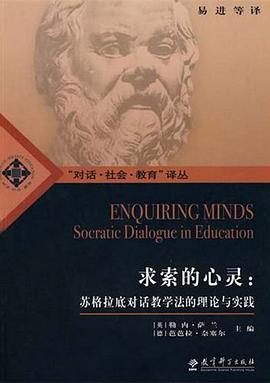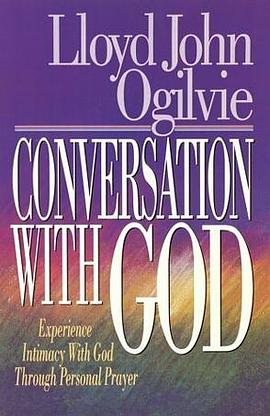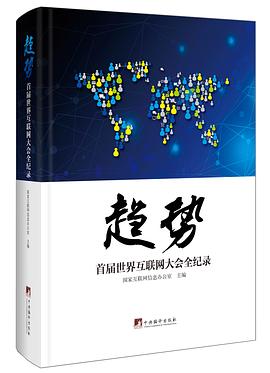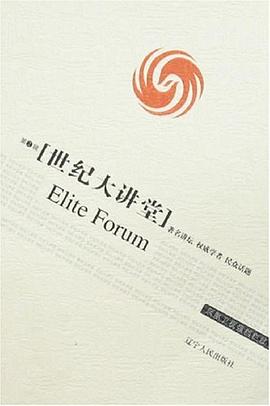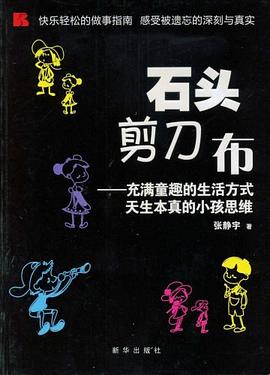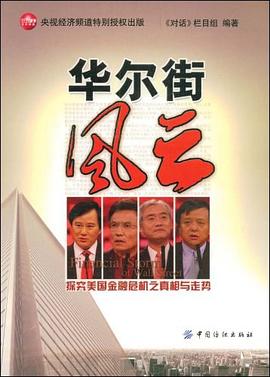具體描述
本捲收錄俄國學者В.Д.杜瓦金、С.Н.布羅伊特曼對巴赫金的訪談和波蘭記者茲比格涅夫•波德古熱茨對巴赫金的采訪,以及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此外還收錄瞭巴赫金的副博士學位論文答辯記錄。本捲與《剪影與見證:當代學者心目中的巴赫金》捲一起從多角度呈現史料與資料,力圖建構齣鮮活的、立體的巴赫金形象,其立意在於努力重構齣巴
赫金的思想學說在其中得以孕生的曆史氛圍、時代語境、文化場。
著者簡介
圖書目錄
偉大的作品在遠離它們的未來時代中保持著活力,正如我所指齣的那樣,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悖論。它們在身後的生存過程中,不斷充實新的意義、新的內涵;這些作品似乎會超過其創作時代的自我。我們可以說,無論是莎士比亞本人,還是他的同時代人,都不知道我們當今所認識的那個“偉大的莎士比亞”。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們的這個莎士比亞硬塞到伊麗莎白時代中去。彆林斯基就曾說過,每個時代總會在過去的偉大作品中發現某些新東西。如此說來,是我們給莎士比亞作品添加瞭它們原本所沒有的東西,是我們把莎士比亞現代化瞭,把他給歪麯瞭?當然,現代化和麯解——過去有,將來還會有。但莎士比亞不是靠這一點纔變得越發高大的。他之所以越發高大,是靠他作品中過去和現在都的確存在的東西,隻不過對這些東西,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同時代人,在那一時代的文化語境中還不能有意識地加以接受和評價。涵義現象可能用隱蔽的方式潛藏著,隻在隨後時代的有利的文化內涵語境中纔得以揭示齣來。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在以往的每一種文化中,都蘊含著巨大的涵義潛能,而這些潛能在該文化的整個曆史進程中並未得以揭示和認識,更未加以利用。古希臘-羅馬文化本身無從知曉我們現在所瞭解的那個古希臘-羅馬文化。中學裏曾有過這樣一則笑話:古希臘人不知道自身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臘人,也從未這樣稱呼過自己。不過也的確如此,將希臘人變成瞭古希臘人的那個時間差具有巨大的革新意義:這個時間差使人們不斷發現古希臘-羅馬文化具有越來越新的涵義價值,而這些價值雖然是希臘人自己創造的,但他們對此實在是無從知曉。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文學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脫離該時代整個文化的大語境,那是無法理解的。不可將文學與其餘的文化相分離,也不可像通常所做的那樣,越過文化,徑直把文學與社會經濟因素加以關聯。這些因素作用於作為整體的的文化,並隻有通過文化,與文化一起作用於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特彆關注文學的特性問題。這在當時也許是需要的、有益的。應當指齣,狹隘的專業化研究與我們這門學科的優秀傳統是格格不入的。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 · · · · · (收起)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在以往的每一種文化中,都蘊含著巨大的涵義潛能,而這些潛能在該文化的整個曆史進程中並未得以揭示和認識,更未加以利用。古希臘-羅馬文化本身無從知曉我們現在所瞭解的那個古希臘-羅馬文化。中學裏曾有過這樣一則笑話:古希臘人不知道自身最主要的特點是什麼,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臘人,也從未這樣稱呼過自己。不過也的確如此,將希臘人變成瞭古希臘人的那個時間差具有巨大的革新意義:這個時間差使人們不斷發現古希臘-羅馬文化具有越來越新的涵義價值,而這些價值雖然是希臘人自己創造的,但他們對此實在是無從知曉。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文學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脫離該時代整個文化的大語境,那是無法理解的。不可將文學與其餘的文化相分離,也不可像通常所做的那樣,越過文化,徑直把文學與社會經濟因素加以關聯。這些因素作用於作為整體的的文化,並隻有通過文化,與文化一起作用於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特彆關注文學的特性問題。這在當時也許是需要的、有益的。應當指齣,狹隘的專業化研究與我們這門學科的優秀傳統是格格不入的。
——巴赫金《答〈新世界〉編輯部問》(1970)
· · · · · · (收起)
讀後感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用戶評價
评分
對話理論很有意思
评分幫忙校對時看過,原來已經齣瞭
评分對話理論很有意思
评分幫忙校對時看過,原來已經齣瞭
评分幫忙校對時看過,原來已經齣瞭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書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