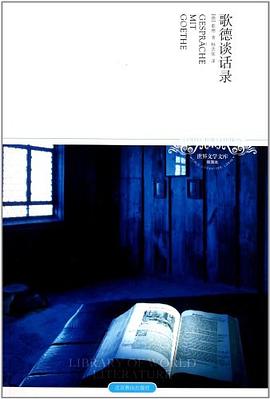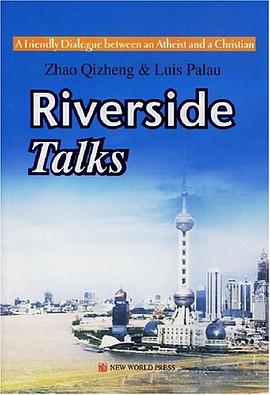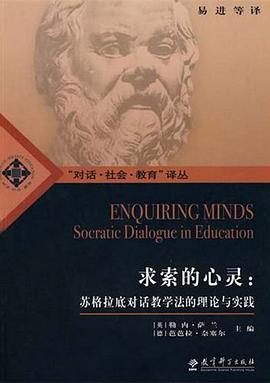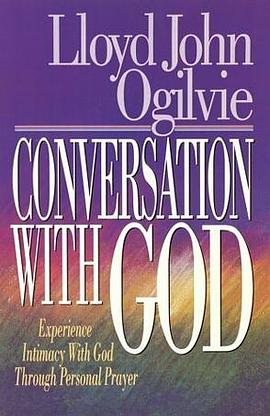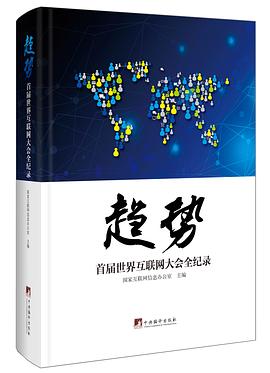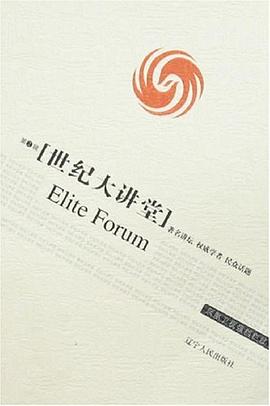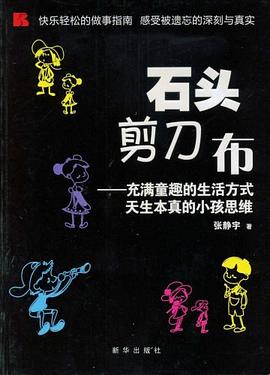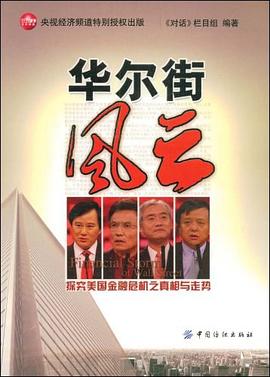具体描述
本卷收录俄国学者В.Д.杜瓦金、С.Н.布罗伊特曼对巴赫金的访谈和波兰记者兹比格涅夫•波德古热茨对巴赫金的采访,以及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此外还收录了巴赫金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录。本卷与《剪影与见证: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卷一起从多角度呈现史料与资料,力图建构出鲜活的、立体的巴赫金形象,其立意在于努力重构出巴
赫金的思想学说在其中得以孕生的历史氛围、时代语境、文化场。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970)
在以往的每一种文化中,都蕴含着巨大的涵义潜能,而这些潜能在该文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并未得以揭示和认识,更未加以利用。古希腊-罗马文化本身无从知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学里曾有过这样一则笑话:古希腊人不知道自身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腊人,也从未这样称呼过自己。不过也的确如此,将希腊人变成了古希腊人的那个时间差具有巨大的革新意义:这个时间差使人们不断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具有越来越新的涵义价值,而这些价值虽然是希腊人自己创造的,但他们对此实在是无从知晓。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970)
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脱离该时代整个文化的大语境,那是无法理解的。不可将文学与其余的文化相分离,也不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径直把文学与社会经济因素加以关联。这些因素作用于作为整体的的文化,并只有通过文化,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特别关注文学的特性问题。这在当时也许是需要的、有益的。应当指出,狭隘的专业化研究与我们这门学科的优秀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970)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刚拿到这本书,还没来得及细读,但仅仅是翻阅,就已经被它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前沿的理论思辨所吸引。书名《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本身就充满了引人探索的意味,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充满思想碰撞和智慧火花的场域。我一直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深感兴趣,它为理解文学、语言乃至人际互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打破了单向度的灌输模式,强调了主体间性的重要性。这本书能够将巴赫金本人置于“对话”之中,通过访谈与笔谈的形式来呈现其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研究方法。我期待着从中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巴赫金的核心概念,例如“复调性”、“狂欢化”、“对话性”等,以及这些概念是如何在他自己的思想探索过程中不断演化和丰富的。同时,我也很好奇,在与不同访谈者和对话者的互动中,巴赫金的思想是否会呈现出新的面向,或者是否会因为对话的语境而产生意想不到的解读。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绝佳机会,让我迫不及待地想沉浸其中,与巴赫金在思想的海洋中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
评分这本书的纸张质感非常好,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书墨香,光是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它蕴含的厚重感。巴赫金,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遥远而略显艰涩的理论符号,但对我而言,他更像是一位一直在邀请我们加入他思想探索的伙伴。他的“对话”理论,不仅仅是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更是对我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与他人沟通的一种启示。这本书以访谈和笔谈的方式呈现巴赫金,这是一种多么“巴赫金式”的呈现方式啊!它本身就充满了对话的意味,将我们读者置于一种主动参与、积极互动的状态。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些访谈和笔谈的内容,是否能揭示巴赫金在面对不同问题时,思想的细微之处?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论,又如何与那些试图理解或误读他的人进行交流?这本书似乎是打开巴赫金思想大门的另一把关键钥匙,它将帮助我更立体、更鲜活地理解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评分这本书的封套设计十分讲究,细致的纹理和内敛的色彩传递出一种深厚的学术底蕴。巴赫金,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无数的学者。我一直对他的“对话性”理论非常着迷,它为理解文学的意义生产和主体间性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然而,理论著作往往存在一定的阅读门槛,《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加亲切的途径来接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我期待在访谈中,能够听到巴赫金本人是如何阐述他的核心概念,如何回应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学术领域的提问;在笔谈中,我希望能够看到他与其他思想家之间那种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从中体会到理论发展的动态过程。这本书不仅是对巴赫金思想的梳理,更是对他思想生命力的呈现,它将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其理论的精髓,并将其运用到我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去启迪更多的学生。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就透着一股沉静而又不失力量的格调,封面的设计感十足,仿佛在诉说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学术传承。我一直认为,阅读一部关于思想家的著作,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更是一种与智者对话的体验。而《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绝佳的平台。巴赫金的名字,对于任何一个热爱文学、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人来说,都如同一个闪耀的星辰,指引着我们探索更广阔的理论天空。他的“对话理论”更是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学术认知,将文学的意义生产从作者的单一意图解放出来,强调了读者、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复杂而动态的互动关系。这本书通过访谈与笔谈的形式,将巴赫金本人置于一个鲜活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借此窥见这位思想巨匠在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思考轨迹,以及他如何回应来自不同角度的提问与挑战。我特别期待书中能有对巴赫金创作生涯中一些关键时刻的深入访谈,或者他与其他学者之间关于核心概念的辩论性笔谈,这将极大地帮助我理解其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评分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精美的排版和清晰的字体,这为接下来的阅读体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巴赫金的名字,在我学习文学理论的道路上,一直扮演着指引者的角色。他的“对话性”理论,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理解文学和语言互动机制的路径,打破了以往许多僵化的理论框架。然而,理论的理解往往需要与实践的结合,而这本书通过“访谈与笔谈”这种形式,无疑将理论家的思想置于一个动态的、互动性的语境中。我非常好奇,在这些访谈和笔谈中,巴赫金是如何回应那些对他理论的质疑和阐释?他的思想在不同的对话情境下,是否会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深度?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对巴赫金思想的总结,更是对其思想发展过程的一种记录,它让我们能够更接近这位思想巨匠的心灵,去感受他思想的鲜活与力量。我期待从中学习如何更灵活地运用巴赫金的理论来分析当代文学作品,以及更深入地理解语言在社会文化互动中的作用。
评分这本书的书脊设计简洁而大气,散发着一种经典的学术气息,正如巴赫金本人在学术界所占据的崇高地位一样。我对巴赫金的研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尤其对其“复调性”理论情有独钟,它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提供了独到的见解。而《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这本书,顾名思义,似乎就是要将巴赫金本人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以一种更具生命力、更接地气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访谈和笔谈,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他的思考过程,他的疑惑,以及他如何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与不同背景的访谈者交流时,巴赫金是否会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在与同行的笔谈中,他是否会表现出学术研究中常见的那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份关于思想生成过程的珍贵记录,它将帮助我更全面地理解巴赫金的思想体系,并且为我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评分我最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语言哲学和文化批评的研究,而巴赫金的理论体系在这两个领域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当我在书店看到《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这本书时,我的目光立刻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的书名就充满了学术探索的张力,它预示着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思想的“现场”,去倾听巴赫金本人最真实的声音。我一直对巴赫金的“狂欢化”和“复调性”等概念颇有研究,但有时会觉得理论本身过于抽象,难以把握其形成的全过程。通过访谈和笔谈的形式,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巴赫金是如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打磨和发展他的思想的。我特别好奇,在这些对话中,巴赫金是否会触及到一些在他著作中未曾充分展开的观点?他如何回应那些对他理论的批评和质疑?这本书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能够从更微观、更具象的层面去理解巴赫金的学术贡献,并且从中获得启发,将他的思想更加灵活地运用到我的研究之中。
评分我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到如此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供的视角非常独特。巴赫金作为一位对文学、语言和社会文化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早已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基石。但我们往往是从他人的解读中去认识他,而《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这本书,则试图让我们直接“对话”巴赫金本人。书名中的“访谈”和“笔谈”就暗示了一种直接的、非媒介化的交流方式,这对于理解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演变和核心关切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我一直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他关于“狂欢化”的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尝试将其应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现象。而这本书,我相信能够为我提供更深入的洞见,让我了解巴赫金本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他是否会关注到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本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思想的“在场”,它将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巴赫金思想的活力与生命力。
评分我个人一直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流派颇有研究,而巴赫金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他的“对话性”思想,在我看来,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理论的革新,更是对人类认知方式的一种深刻反思。这本书的出现,无疑填补了我在这方面的某些空白。能够通过访谈和笔谈这样一种相对直接而又不失深度的形式来呈现巴赫金的思想,这本身就极具吸引力。我设想,在那些访谈片段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巴赫金在回答问题时,那些富有洞察力的瞬间,他如何精准地界定概念,如何巧妙地运用例子来阐述复杂的理论。而在笔谈部分,我更期待看到他与其他思想家之间思想交锋的火花,那种字斟句酌、逻辑严谨的论辩,无疑是思想的盛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超越二手研究的局限,更接近巴赫金思想的源头,去感受他思想的鲜活与力量。我希望能从中学习到如何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更有效地运用到我的学术研究中,例如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或者探讨更广泛的文化现象。
评分我一直相信,伟大的思想家不仅在于他们提出了多么深刻的理论,更在于他们如何与世界进行持续的对话。而《对话中的巴赫金:访谈与笔谈》这本书,正是这样一种对思想家生命力的捕捉。巴赫金的名字,对我来说,代表着一种颠覆性的思维方式,一种对传统规范的挑战,以及对人类主体间性关系的深刻洞察。他的“对话理论”我已经研读多时,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渴望能更深入地触及理论的“生产过程”。这本书通过访谈和笔谈的形式,为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能够“亲身”参与到巴赫金的思想世界中。我期待在书中找到那些关于他核心概念的形成过程,他如何回应批评,如何与其他学者交流的真实记录。这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一种思想的浸润,一种与智慧擦肩而过的体验。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更好地理解巴赫金思想的深层逻辑,并且将其灵活性和开放性运用到我的学术探索中,去发现更多隐藏在文本和生活中的“对话”。
评分帮忙校对时看过,原来已经出了
评分帮忙校对时看过,原来已经出了
评分帮忙校对时看过,原来已经出了
评分对话理论很有意思
评分帮忙校对时看过,原来已经出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