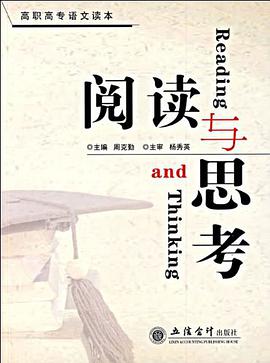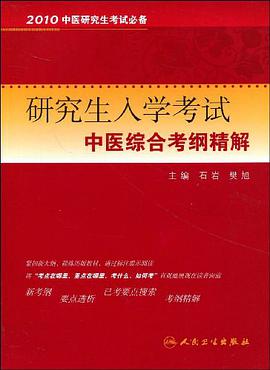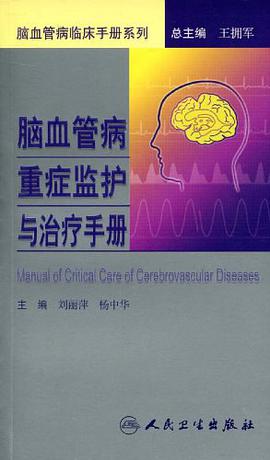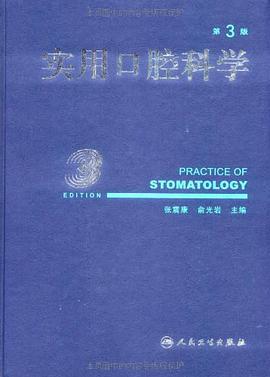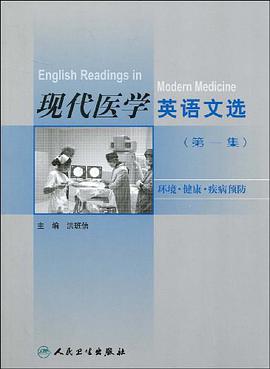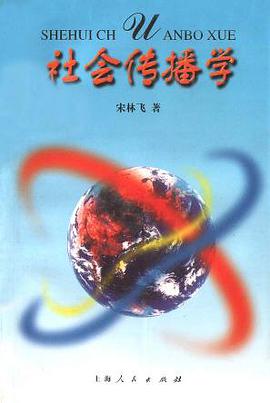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的著者吴永章先生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的民族政策”,二是“畲、瑶、苗的‘游耕’生产方式”,即在外来强势武力、进步文明的挤压之下游耕文明的节节败退。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当今世界的冲突归结为几个文明的冲突,而谈到中华文明时,他认为:“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亨廷顿先生承认,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明为纽带连成的文明圈,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传统的儒家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可以说,农耕或土地就是儒家文明的载体。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以农耕为载体的、内敛惰性、缺乏张力的农业文明在近代面对以海洋为载体的、外向扩张、富有流动活力的商业文明的挑战的时候处于明显的弱势,在此,儒家文明成了近代中国失利于国际竞争的替罪羊。这当然是题外话,但如果考察儒家文明的扩张过程时,我们会发现,这种以农耕为本的文明,在南下与以游耕为本的南方“荆蛮”文明(暂且这么命名)碰撞时往往可以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儒家文明在中国南方的扩张虽然也是漫长血腥的,但毕竟在南方永远扎下了根,取代了那些“荆蛮”文明而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还辐射到同样以农耕为本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但是,儒家文明在北上遇到以游牧为载体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时候,它却全面败下阵来。如海洋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外向扩张、流动性的,只是它是面向有草地的平原扩张,固守在土地上、缺乏流动的儒家文明不可能皈依这些在大草原上来去不定、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文明,因此,儒家文明从来就没有真正驱赶喇嘛教、萨满教而将影响扩展到蒙古、西藏和中国东北,也没有归顺突厥人、匈奴人、女真人、契丹人,中原汉民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一直都隐喻着这两种文明的互相碰撞和征服,儒家文明和游牧文明始终都处于时战时和的紧张关系中。有意思的是,两个曾经统治过中国的游牧民族,一个固守游牧民族痼疾却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为儒家文明打败而灰溜溜地回大草原牧羊,而另一个则识时务地为儒家文明所浇灌而打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华帝国。
所以,如果用历史的远程望远镜来审视亨廷顿先生的世界大文明圈中的中华文明,那么,更应将它发展成势的过程视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游耕文明的斗争与反斗争、征服与反征服的漫长过程。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游耕文明“逐山而生”,那么,农耕文明就是逐土地而生,哪里有土地,农耕民族就趋之若鹜。以农耕或土地为载体的儒家文明的南征北扩大致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君主帝王的政治抱负和丰功伟绩的荣誉心理。开疆扩土、极大化统治区域是每个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如汉帝王就曾多次派军队“围剿”“武陵蛮”,汉名将马援还因此丧命。第二,中国历史上多次乱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国历史时治时乱,治乱相间,几次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冲击了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游耕民族。第三,农耕文明的死穴。农耕以土地为本,机器时代之前的农业操作以人口多为荣,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对土地的供求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引起对土地的无度追求,农耕逐渐朝山林、草原扩张,梯田、牧田数量不断增加,悄悄蚕食了游牧、游耕民族的生存空间。从主观动机而言,我们不能说以上的几个原因犹如美国的西进运动那样,是有目的有企图地对游牧、游耕民族进行驱逐控制或同化,但从客观效果而言,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游牧、游耕民族的节节败退和游牧、游耕文明的式微。
“食尽一山,复往一山”〔2〕,“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3〕,“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4〕,这是游耕文明的基本特点。显然,这种“刀耕火种”的文明处于比较原始、程度较低的古代文明水平。现在的畲瑶苗人固然已经摆脱了这种古代文明的以靠山吃山形式对大自然的野蛮操作,逐渐向以农耕为主的农业靠拢,但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畲、瑶、苗却一直赖以游耕为生存方式,在游耕的生活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因此,不论是以马克思对文明的界定、还是以亨廷顿先生对文明的划分来定义畲瑶苗,三族由于共同的渊源都可以形成为一个小文明,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覆盖之下的小文明,这个小文明暂且命名为“荆蛮”文明。
其实,中华文明就是由如“荆蛮”文明这样的无数个小文明与儒家文明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不断融合的过程。例如,“晋代的陶侃原是溪族,而他的后裔陶渊明却是汉族田园诗之祖先了;北魏的皇族拓跋氏迁都洛阳后改为元氏,到了唐代,元稹已是汉族名臣,是元和诗体的代表;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考其血统,分别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胡人及匈奴人后裔”〔5〕。因此,说中华文明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出来的,是比较中肯、合乎历史的。现在,这些民族可能属于少数民族,这些文明在中华大文明中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文明,但是在百年千年之前,他们都曾经是生存土地上的主人。那时候,相对于汉民族,相对于儒家文明,他们可不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古代文明也不是小文明。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蒙先生提到的在美国四十多万瑶苗族人。从如今的鄂湘地区飘洋过海到美洲,瑶苗人颠沛流离、奔走他乡的距离可以说是“路漫漫”,人口之众已达到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五分之一强(据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现在居住国外的苗人大多是在1975年老挝内战之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安排下,寻求政治、战争避难陆续到达所居住国家的。1975年老挝政府军队就开始对由美国支持的以青年军官王宝为首的苗族武装势力进行围剿,给苗人(武装势力和平民百姓)造成了重大伤亡。逃亡国外的王宝声称:“1975年至1978年间有五万苗人死于人民解放军的化学毒药,而另有四万五千人殁于饥饿、疾病或在试图逃往泰国途中被枪杀。”“据1990年估计,超过九万人的苗族难民已经逃难到美国,法国有六千人,有三千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法属圭亚那。”〔6〕至1999年,在美瑶人也达到三万六千人。现在定居美国的瑶苗人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生活社区,其中就有全美瑶人协会。但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观念的差异,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也没能够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在苦苦争取美国公民的身份。
现在,每年都有不少的海外瑶苗族人回大陆寻访祖先的故土,参加盘王庆典活动。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寻亲访祖,但另一方面又是长期生活在不同文明的社会里,与不同的文明碰撞摩擦后对自身文明的一种回归。一些敏锐的学者也认识到,亨廷顿先生之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框架下,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强,一些美国种族主义者认为的WASP(Anglo-Saxon White Person,盎格鲁-萨克森白人)的“种族优势”正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所“侵蚀”,新教将逐渐失去相对于儒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优势”(实际上就是马克斯 · 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作用)。由此,亨廷顿先生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对基督教文明的未来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种族血统和宗教信仰都有别于美国主流的瑶苗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基督教文明中生存,必然会受到美国主流文明的冲击和挑战。美国虽是个民主的社会,但也是个等级社会,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一个自觉世间惟有耶稣可以拯救世人的社会,基督教徒在待人宽容博爱中也在渐渐向外输送基督教的教义并劝导你“皈依我主”,这正是第一代瑶苗移民的担忧之处。同在美的第一代藏人一样,第一代的瑶苗移民尚且可以保持自身民族的特点,而在第二代身上,他们已经隐隐感觉到美国文明正在渐渐渗入他们后辈的体内,以及他们的后辈在对待自身的民族特性方面的不屑和怠慢。据一些美国的苗族老人说,现在的美国苗族青年已开始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非常担心最终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正在寻求保持传统文化的方法。不妨学习亨廷顿先生的“忧患意识”,对于这些在海外的瑶苗人,对于他们的小文明在其他文明的国度里的命运,暂且也怀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吧。
作者简介
吴永章,1936年生11月生,男,汉族,广东梅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制)。获学士学位。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特聘教授。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有: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百越民族研究会顾问;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瑶学会执行委员等。曾多次被国家社会基金委员会、教育部有关单位、学术委员会亲聘为评审专家。
长期从事中国南方民族(包括客家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著有《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中国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题解》等学术性著作十部。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共计四百余万字。曾先后六次获得省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2004年完成了全国社科基金项目《湘鄂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史》。其论著先后获省部与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著作二等奖。《瑶族史》获国家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著作二等奖。前辈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曾称赞他的研究"非常优异,特别对中国民族学史志方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目录信息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得很有逻辑性,仿佛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由表及里的探索之旅。一开始通常会从地理环境入手,勾勒出畲族和瑶苗聚居地的自然环境特征,接着自然过渡到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对比。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的比较部分。不同版本的创世神话,往往能折射出族群最核心的世界观和价值取而。书中对两者在祭祀祖先、崇拜自然神灵方面的细微差别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这一点让我深感震撼。例如,某个瑶族支系对特定山神的祭祀仪式细节,与某个畲族宗族的家神崇拜,虽然表面相似,但其背后的社会功能和权力结构却大相径庭。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落实到了具体的仪式动作和口头叙事之中,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图景鲜活起来。唯一的小遗憾是,希望在对现代性冲击的论述上能再多一些当代青年的声音,毕竟文化传承的主体是人,他们的感受和选择同样重要。
评分读完这本书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的学术功底深厚,但叙述方式略显学院派,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可能需要一定的耐心去消化那些专业术语和复杂的理论框架。不过,一旦沉下心去阅读,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的知识密度非常惊人。书中对畲族和瑶苗的谱系学考证部分尤为精彩,它不仅仅罗列事实,更是试图构建一个更宏大的族群迁徙和演变的历史图景。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文化变迁”议题时的审慎态度,没有简单地用“消亡”或“保护”这种二元对立的词汇来概括,而是细致地描绘了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展现出的适应性与韧性。比如,他们对于土地、山林资源的观念差异,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他们的经济模式和政治联盟的形成?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分析,是普通旅游指南或普及读物无法提供的。总体来说,这是一部需要细嚼慢咽的学术精品,适合对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有一定基础的读者深入研读。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挺吸引人的,关于畲族和瑶苗的比较研究,感觉内容会非常扎实。我最近对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特别是他们之间的互动与差异。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给人一种厚重感,感觉像是经过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深入剖析这两个族群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上的异同点。比如,在婚丧嫁娶这些重大仪式上,他们是如何互相影响又各自保持特色的?还有在与外界,特别是汉族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适应和抵抗策略又是怎样的?我特别想了解的是,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他们的传统文化正在面临怎样的挑战,以及他们内部是如何努力去传承和创新的。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到的见解,而不是泛泛而谈的介绍。如果能配上一些高质量的田野照片或者地图资料,那就更完美了,能帮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这些山地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景观。总而言之,我对这本书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它能成为我了解这些西南边陲民族的权威参考。
评分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的论述是严谨且克制的,作者明显倾向于客观描述和谨慎推论,避免了将复杂的民族问题简单化或浪漫化的倾向,这点我非常欣赏。它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学术笔触,探讨了诸如土地制度变迁、外来宗教渗透以及民族身份认同重塑等敏感议题。特别是关于畲族与瑶苗在近代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书中引用的清代档案和民国时期的地方法志资料非常丰富,为我们理解他们如何在中国多重权力结构下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这种对历史语境的深度挖掘,让读者认识到,所谓的“传统文化”并非真空中的产物,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与塑造。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严肃对待研究对象,并以高质量的文献和田野为基础的学术力作,对于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南方山地民族社会变迁脉络的人来说,绝对值得入手细读和收藏。
评分这本研究专著的价值在于其跨学科的视野。它不仅仅是一本民族志,更像是一部社会历史地理学的综合报告。作者似乎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我注意到书中对“苗瑶语族”内部的语言分化和地理分布进行了专业的梳理,这对于理解他们如何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中维持或重塑族群认同至关重要。这种多维度的分析方法,避免了将少数民族简单地视为静态的“文化标本”来研究的窠臼。相反,它展现了畲族和瑶苗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动、适应、重构自身的动态群体。通过对他们历史上的商业网络和人口迁移路径的分析,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边界”是如何被建构和跨越的。对于研究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其论据的翔实程度令人信服,很多观点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深入解读。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quotespace.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美书屋 版权所有